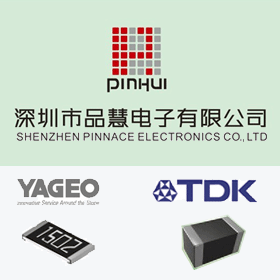网约车司机的一次别离
撰文 | 文烨豪 ?
编辑 | 吴先之
又有乘客在司机到达上车点后取消了订单:对网约车司机王军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那是一个下雨的晚高峰,王军在高德接到了3公里外的订单,马上一刻也不敢耽误地赶过去,在他经过漫长的堵车终于到达上车点后,乘客挂掉了他的电话,不久平台发来一条熟悉的消息模版:稍等马上到。
十分钟之后,王军没有等到乘客,但等到了系统的提示:“乘客取消了订单”。
没有空驶补偿,占用了晚高峰时间,这都不算什么,让王军最难以接受的,是上一次乘客这样取消订单后,一个猩红的叹号跳出来,提醒他被系统判定违规,违规原因是“未接乘客”。王军马上截了堵车的图片申诉。第二天,申诉被驳回,而他能做的,只是默默调转方向盘,去接下一个订单。
“感觉很委屈,明明不是我们的错,但损失永远是我们在承担。”王军说,有一个同行曾经在被无故取消订单、处罚多次后“摆烂”,一口气接了很多预约单且不去接乘客,以报复平台和乘客:“但是大多数人一般不会这么做,因为我们有基本的良知。”
事实上,这只是网约车司机和高德的矛盾之一——确切地说,应该是网约车司机和聚合平台的矛盾。愤怒的、无奈的、委屈的……红利退潮之后,越来越多的司机浮出地表之上,让高德的结构性矛盾暴露无余。

而另一方面,更多巨头们“摸着高德过河”,试图瓜分其蛋糕。内忧外患下,高德这位聚合打车模式的头号玩家迎来了巨大考验:
矛盾,已到了一触即发的临界点。
对乘客的友好,是对司机的残忍
司机们种种控诉,大多指向高德对乘客的无底线偏袒。然而,高德们崛起的路程,就是一部以低价、更多权益等优惠吸引乘客的司机血泪史。
价值是守恒的,如果平台把权益多分给乘客一分,那么司机就会对应地少一分。
对网约车行业来说,很难真正形成所谓的护城河,毕竟网约车乘客普遍对价格较为敏感,用户迁移成本过低。谁价格低,谁更容易获客,是不争的事实。以曾盛极一时,一度被认为是“网约车拼多多”的花小猪为例,其本质正是滴滴为了绕开自身沉重的体系所扶植出的产物。
只是,这种消耗战,对尚未解禁、盈利的滴滴而言负担过重。纵使滴滴身为龙头,能将司机时薪、车辆耗损等卷到极致,但聚合平台中的“新生力量”为抢占市场,往往会不惜一切代价地讨好乘客。
拿上文的乘客频频取消高德的订单来说,其背后就是高德对乘客的“溺爱”。王军说,在滴滴,用户超过时限后取消订单往往需要支付违约金,然而在高德,只要乘客会员等级达到黄金,每月即有3次免取消费的机会,即便是无理由取消订单,也无需支付违约金。
“那个会员等级是由乘客在高德累计的打车里程数决定的,甚至可以说,高德打车人均黄金会员。有一次我在贴吧看到了一个帖子,是一个乘客分享的‘打车攻略’,他说每次都打高德、美团等好几个聚合平台的车,然后让他们‘赛跑’,谁先到了,就取消另外几个,并为自己节约的时间沾沾自喜。”
王军说,他看到“赛跑”二字的第一反应是好笑,随后是深深的无力感:“毕竟部分乘客能这样欺负我们司机,本质上还是平台纵容,甚至默许的。他也曾向平台索要空驶补偿,最终被客服以渠道单为由给搪塞了过去。”
对网约车司机来说,随着时间推移,可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权益被一点点蚕食:湖南长沙的司机李东亮讲了另一个故事,去年9月,一个乘客下车时说自己的手机会免密支付,然而过了三四天,自己都没有收到乘客的付款。

“因为订单早已结束,通过平台虚拟号码已经联系不上乘客了,向平台申诉也没有结果,难道我们司机就活该给乘客买单?”时隔几个月,李东亮提起这单仍然很愤慨:
“你知道最让我寒心的是什么吗?是当时我给司机端客服打电话,打了几次都没被接通,再试着打乘客端客服,瞬间就接通了,这叫什么事呢?”
于平台而言,乘客和司机就像天平的两端:不断在乘客端加码,就意味着司机端权益的不断被侵蚀。也就是说,聚合平台对乘客的种种讨好行为,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把成本转嫁给司机的“慨他人之慷”:对乘客的友好,对司机却是一种残忍。
订单少、价格低,网约车红利期不再
高德和他的司机们也曾经有过短暂的蜜月期:那是高德刚刚崛起的时候。
尤其是在滴滴下架后,一众网约车平台“趁虚而入”,以门槛低、入驻福利高、免佣金等优惠措施为诱饵,吸引了大批司机入驻。据陈利明回忆,当时各平台给的补贴特别高,他所在的T3出行,每天出车给的奖励甚至比跑车收入还高。
正因如此,陈利明毅然决然地跳入了那波网约车的“易帜浪潮”,憧憬着一个高中学历的人也能有一份月入过万的收入。为此,他成为了网约车司机中的“卷王”——平均每天出车14个小时,甚至还做到过一个月一天不休。“实在没有办法,上有老下有小,两个孩子一个上了初中,一个上了小学,正是用钱的时候”。
彼时,他尚不知道,这只是步入又一座围城的开始,让人眼馋的激励亦不可复制。随着平台之间“抢司机大战”归于平静,行业残酷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随着海量订单涌向高德,司机逐渐从主动到切换为被动状态。
即使像陈利明这样的“肝帝”,这两年也明显感觉,钱越来越难挣了:“现在我一天流水400左右,扣除租车、抽佣、保险、违章费什么的,算下来月入能有6000、7000,这还是拿命跑出来的结果。我们这有些刚跑车的兄弟,一个月到手也就4000、5000。”
而一口价订单等低价获客的模式推出后,更是让司机叫苦不迭。陈利明表示,现在开了一口价订单,根本赚不到什么钱,最低的时候一公里就一块多钱,堵车也不算钱,还没有送外卖划算。但不开一口价订单,订单又太少了,流水跑不起来,根本吃不到平台的单量奖励。
“而且平台的机制很‘鸡贼’,它好像会派在几个一口价订单中给你塞一两个优质订单,吊着我们。”陈利明苦笑到:“这就好比原来打传奇时偶尔爆出点好装备,让你产生错觉,继续往里面投钱。”
其实,陈利明不是没想过换个平台,只是在这个城市,高德的订单是最多的。“就算是滴滴,也不太能一直接到单。”而收入下滑之后,他也曾短暂尝试过像那些车里塞4、5台手机的老司机一样多平台接单,但最终效果适得其反。
陈利明透露:“多平台接单的好处是可以挑乘客,碰到费力不讨好的订单,以没电、车胎被扎等借口打电话给乘客劝他主动取消就行。只是有些乘客明明在电话里答应的好好的,反手就给你一个举报。”
而所有的网约车平台,都遵循着类似的攒分规则——只有订单越多、跑车时间越长,积分才能提升,才更有可能被优先派单。而尝试多平台接单的那段时间,由于积分少,主动取消次数多,他在每个平台都难以升级,派单反而比之前更少。
“最极端的时候,我一天有几小时都是停在路边等待接单。” ?陈利明叹了口气。
而在重庆跑滴滴多年的刘国庆说,滴滴平台现在同样不好接单了,尤其对私家车越来越不友好,要想有更多派单,就得去租滴滴官方提供的车辆。
社会学学者孙慧和赵道静曾指出:网约车司机看似拥有可以自主接单的工作自由,实际上是一种“伪自由”。平台对司机的奖励要求是,司机在特定时间内必须完成一定单量,如早晚高峰时期。而当这些条件与一口价订单等模式绑定时,意味着司机陷入了更大的被动。
重庆网约车的司机刘伟,曾是一家中餐馆的老板。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300多平的门店被迫停业,月赔十万,不得不关了店出来跑网约车过渡。单平台接单、服务态度良好,外加几十年的驾龄,刘伟虽只在鞍马出行注册了两个多月,便已将平台等级升满,一单未完,又接一单。
即便订单不停,想拿到冲单奖励也异常艰难。上周,他8点出车,接近12点收车,才勉强跑完冲单奖励所要求的35单,拿到了高德与鞍马合计60多元的奖励金。
“比开餐馆累多了,而且不是一种累法,开餐馆每天忙得充实,开车纯粹是消耗人。我跑车之后,就算烟、酒都戒了,身体还是遭不住,每天腰酸背痛,就算收车以后,大脑也是开车的飞驰状态,轻飘飘、晕乎乎的。回家后女儿问,爸爸你怎么不陪我耍了?我还哪有力气耍撒。”

对此,司机没有办法与平台抗衡,只能接受或者离开。而放开之后,颇爱折腾的刘伟也决定,再跑半年就不跑了,琢磨点新的机会。
在车上,本还想追问点什么,但终点很快就到了,他也在抵达终点前就接到了下一个单子,随即消失在庞大的车流里,等待他的,是又一个漫长的晚高峰。
平台两头吃,司机叫苦不迭
相较于网约车司机与高德的显性矛盾,其同自身平台的冲突,往往更为隐蔽,也更为激烈。
背后的逻辑在于,“双证”合规浪潮下,当下网约车行业的逻辑,已然从过去的私家车兼职跑车,逐渐向类似出租车的全职的逻辑演变。
沈阳的网约车司机小易,对这几年行业的变迁深有感触。小易只有“人证”,政策出台后,他明显感觉到自己接单的数量骤降:“政策一出,很快我在滴滴接不到什么好订单了,它们好像会优先派单给有双证的司机。”
而随着监管趋严,各大平台也“变本加厉”,从起初的减少派单,到后面直接不予派单。在此背景下,小易只好从滴滴转战审核相对宽松的小平台。“虽然挂靠高德,单价很低,好歹还能再跑跑。”
此外,没有双证的小易,也不敢轻易去到高铁站、机场这些优质订单的“集中地”,毕竟这些地方运管出没相当频繁,没证被逮住一次,就是上万的罚款。
尽管如此,当地还是有老司机“富贵险中求”,在高铁站、机场依然处变不惊。“我有一个朋友,就把平台挂到后台运行,用蓝牙耳机接收消息,被运管问到就说接朋友,刀尖上赚钱。但我最多只敢接车站单,把乘客送到车站附近求他多走两步,没必要冒太多风险。”
其实,小易不是没想过办双证,但他曾算过一笔帐,办“车证”不仅意味着自己的车将成为营运车,跑60万公里或跑8年就得报废,每年还将面临10000多的保险费。“光是保险,摊下来一个月都有一千多,就算我没出车这钱也得花,那我不是被网约车套牢了嘛。”
换言之,一旦拿到双证,就意味着和网约车行业绑定更深,而很多司机,似乎并不愿意绑定在这个消磨人的行业上。“网约车只是个过渡的权宜之计,总不能一辈子跑网约车吧。”
而随着合规铺开,叠加订单下滑、行业内卷加剧等因素,司机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少,不少司机默默换了电车以节约成本,有的司机甚至直接沦为了平台的“打工人”。
阳光出行,作为高德聚合平台中单价最低的那一批玩家,正是遵循着此番逻辑。据一位阳光出行司机透露,相较于过去想跑就跑,不想跑就歇着的时光,如今车是从平台租的,自己更像是平台的员工。“当初签合同时,平台给了我两个选择,一是上班拿底薪,流水大头给平台,超出的部分才归我;一是从平台租车,租金+保险一天200多元。”
显然,此番标准对刚入行的他而言未免显得严苛。“跑了两个多月,才发现很难赚到钱,也想强制退车,但几千押金就打水漂了,只有咬咬牙继续跑,看看放开后能不能好起来。”
换言之,行业盛衰与否,同网约车平台的关系其实不大,即便是乘客端不赚钱亦能接受,只要能靠低价撑起单量,保证平台基本运转即可。其只需投入大量营销成本,铺开广告招募司机,靠车辆租金、会员费,甚至是司机逃离行业所缴的押金度日。

毕竟在这几年的就业环境下,平台精心编织的“月入过万”故事,可谓相当动听。一批批司机自信满满地进入行业,再一批批灰头土脸地黯然离场,平台则坐享渔翁之利。
只是,再动听的故事,亦有被戳穿的一天。退车、逃离,似乎成为了司机们的不约而同的选择,而被退租的车辆,亦堆成了新闻报道里的“网约车坟场”。
平台与司机的矛盾加剧,高德很难成为赢家。
聚合平台的结构性问题
重庆司机赵岩在去年年末与其平台司管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在当时,他已经决定转行,并立即退车,在签合同时,租车公司说退车时30天内就能走完流程,然而在真正想要退车时,本应在一个月内退还的押金,拖了两个多月迟迟未退。
“之所以想方设法不让我们退车?还不是把我们当韭菜割。总有人活不下去了要去跑车的,他们早就看准了。”赵岩说,“现在不仅拖着押金不退,退车前这一个月的未支付订单,他们也不给我们结算。”
赵岩所租的车单月押金接近4000元,疫情期间有几个月根本不赚钱,却依然要交租车费用和佣金,就算顺延了一个月,压力也很大,现在几乎属于“贷款上班”。此外,据他透露,几乎所有有租车业务的平台,似乎都会优先给租他们车的司机派单,这也让他断了买新车,然后“以跑养车”的念想。
而在这场司机、租车公司、高德、乘客四方的对峙中,夹在中间的高德往往最为无力与焦灼。
作为聚合打车平台,高德无疑是最不希望司机大量流失的那一方。可以看到,攻守易势下,高德也出台了很多举措挽留:
在乘客端,单价更高的“免佣联盟精选司机”,在打车页面占据了中心位置。司机端,则是在早高峰节假日期间为司机免佣金,并同网约车平台合作,推出针对新司机的拉新活动。
只是,受限于聚合平台的特性,高德的安抚措施,在溃退的司机大军中,略显苍白无力。毕竟聚合打法虽能通过轻资产模式快速铺开业务,但相较于亲力亲为的滴滴,高德更像是提供流量入口的中介,很难深度介入服务链条。
高德在司机资源上存在结构性问题,纵使各平台已经乱成了一锅粥,高德能做出的行动亦十分有限——没法直面司机,亦没法真正给到司机福利,很难调和平台和司机的“家务事”。
从高德的安抚措施来看,即便“免佣联盟精选司机”被优先推送,但也无法改变乘客多方比价后选择更便宜的特惠单下单的现状。延长免佣时长等活动亦是治标不治本,赵岩说,早晚高峰虽然免佣金,但往往都被堵车虚耗了。
正如其在新司机招募页面中所展现的“单量多”一般,于高德而言,不论活动多么频繁,其真正能圈住司机的仍是“流量”所带来的海量订单。
然而,纵使是“流量”壁垒,当下亦正遭华为、腾讯、字节等玩家的冲击。
去年7月,华为面向会员开始众测“Pelal出行”,在北京、深圳等城市提供聚合出行服务;同月,腾讯在微信“出行服务”中测试打车功能;而去年末,则有媒体曝出抖音已经开放交通出行服务的平台服务商入驻资格。
值得一提的是,抖音入驻资格一开放,T3出行便在抖音上线了“T3打车”小程序。而在此之前,据一位T3司机透露,在其所在的城市,T3有一半订单来源于其App,一半订单来源于高德,其他渠道基本可以忽略。
而当下,“其他渠道”正在崛起,其中不乏腾讯、抖音等的玩家,高德引以为傲的“流量”,或将遭到分食。可以预见,随着新入场玩家的涌入,聚合打车平台间的竞争将愈发激烈,拼补贴,拼权益,“赔本赚吆喝”,很可能仍将在未来成为常态。
在巨头们“权力的游戏”中,司机却逐渐清醒,留给行业一个寂寥的背影。正如小易所言:
“元旦节期间订单很多,放在以前,我肯定会对新的一年充满期待,但现在,更多的是疲惫与前途的渺茫。”尽管还怀揣着微薄的希望,但其实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网约车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原文标题?:?网约车司机的一次别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