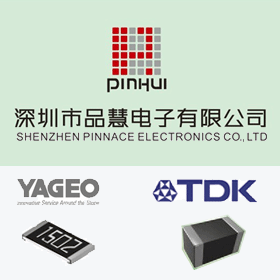《流浪地球2》里的意识上传,真的能让人得救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果壳 (ID:Guokr42),作者:邓思渊,编辑:卧虫、沈知涵,原文标题:《不能细想!〈流浪地球2〉里的意识上传,上传的到底是谁?》,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为什么在《流浪地球 2》中,地球联合政府将“数字生命计划”列为非法?
电影里实际上并没有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意识上传、人类数字化是一个经典的科幻命题,而且数字生命计划本身就很有说服力:相比于投入巨大看上去几乎不可行的建造一万台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的“移山计划”,数字生命计划看上去诱惑力大多了:只需要将全人类都上传到计算机里,然后把这台计算机装进飞船里带走,人类不就得以延续下去了吗?

“没有人的文明,毫无意义”丨流浪地球 2 预告片
那么,我们就要面对两个问题:人类意识上传,做得到吗?这是能力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在电影中的那样一个时空背景下)选择数字生命计划拯救人类?这是道德问题。
不仅仅数字化大脑那么简单
长久以来,我们对于人类意识和身体的直观认知,大概总结成一个术语,就是“身心二元论”:我们的心灵就像住在我们头脑之中的小人,通过眼睛的窗户向外张望。那么既然我们的心灵是小人,只是居住在我们的身体之中,那么自然的推论就是这个小人也可以居住在其他的地方,比方说电脑里。
现代科学对于大脑的研究已经表明,“身心二元论”是一种错误的想象。我们的意识或者说心灵,实际上是大脑中的大量神经元之间脉冲互动的一种表现。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大脑中有某种特殊的区域或者结构,专门留给“自我意识”的储藏。而传统意义上的“自我意识”很大程度上是大脑的各个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互动的一种结果,甚至有人会把这理解为一种“幻觉”。
因此,想要想将人的意识数字化,就必须研究大脑的基本结构,将意识和大脑的基本结构之间的关系彻底搞清楚之后,才谈得上“上传意识”。既然人类大脑是目前整个宇宙中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种能够思考的物理硬件,那么研究人类大脑和研究人工智能很可能会成为殊途同归的一件事情。
可以这么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真正能够发明出强人工智能,那么意识上传就不远了。
随着现代认知科学对于人类大脑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我们就发现传统的“身心二元论”不但不正确,甚至错得离谱。我们的意识不光是由我们的大脑硬件决定,而且与我们的身体密切相关。在认知科学,这被称为具身认知。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是否饥饿会决定你对于食物的认知,人很难抵御饥饿的时候吃东西的诱惑,这也是为什么减肥这么困难的原因。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心情好,他就会对周围的人面露微笑,然而实际上认知科学家实验发现,如果强迫一个人微笑,他的心情会也因为微笑变好。
实际上人类大脑的活动有很大的一部分都不被你的“自我意识”所决定,而是反过来的,你的自我意识有很大一部分是被你的大脑的活动所决定,“自我意识”做的只是事后找补。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 · 海特(Jonathan Haidt)将这些现象称之为“象与骑象人”:你的意识是骑象人,你的大脑则是大象。在一些偶然的情况下,骑象人能够指挥大象如何行动,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大象自行其事。
所以,我们如果要将意识数字化,不但需要模拟整个大脑,还要模拟整个身体,乃至是周遭世界。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人类的彻底的数字模型和对世界的精细的模拟,才能够让一个人类的数字意识能够正常的运转,这可能比制造一台地球发动机要更加困难。
是复制还是剪切?
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假如我们真的能够模拟出一个人类的数字意识,比方说就是上传了你自己的数字意识,那么:你和你的数字意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黑镜》“USS Callister”,男主创造了一个游戏,其中角色是现实世界里的同事的数字副本,他们在虚拟世界里陪着男主演戏丨Netflix
假设我们已经发明了一套超先进的全脑扫描系统,能够将你的大脑数字化并且上传至计算机,这实际上是一种意识的“复制”,而不是意识的“上传”,这两者是存在重大的区别的。
“上传”实际上意味着你本人的自我意识搬到并存活在了另外一个数字世界里面;而意识的“复制”,只是说有一个你自己的“副本”活在了那个数字世界里面,而不影响你本人仍然活在现实世界之中。这当然会导致一系列的形而上问题,比方说哲学上最基本的那个问题:我是谁?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两个我,那么谁才是真的我呢?是这个在物理世界中的我,还是那个在数字世界中的我?
而在流浪地球的世界观中,这个问题变得更加重要。这种重要性并不仅仅是哲学意义上的,更是现实意义上的:“数字生命计划”拯救的那个人类文明,实际上只是抽象的人类文明,而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个体。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你参加了数字生命计划,你来到了计划的现场,有一台超先进的机器,将你的大脑和你的整个身体扫描上传进了计算机,你在大屏幕上看见了另外一个你自己,这个你自己告诉你,他现在感觉很好,而且他很清楚地知道他将会永远的活下去,而你却只能跟着地球一起灭亡。
这就是“数字生命计划”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意识上传,本质上是“复制”,而不是“剪切”。数字的你睁开眼睛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数字世界之中,而真实的你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在参加了数字生命计划的之前和之后,仍然要面对相同的命运。

《剪草人》(1992),皮尔斯·布鲁斯南将杰夫·法赫的意识困在了一台电脑里丨《剪草人》
这种情况下,可以推想,普通民众在参加了数字生命计划之后会发现自己受到了巨大的欺骗和误导。他们本以为“数字生命计划”是在拯救他们的个体,而实际上并不是。“数字生命计划”仍然是在拯救一个抽象的人类文明(在这里我们暂时不讨论一个数字意识的人类世界,到底能不能算作人类文明或者说是人类文明的某种延续的变体),而并非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当人们慢慢理解到这一点之后,还有多少人会真的支持数字生命计划呢?相比之下,“移山计划”才是拯救每一个具体的人的方案。
但如果我们讨论的并不是在流浪地球那样的背景下一个紧迫的末日环境,那么我认为意识上传或许真的是人类文明的下一步。而我们也有可能真的找到一种让意识上传变成“剪切”而非“复制”的手段。或许我们离这一个目标并不是很遥远,没准在我们有生之年就能实现呢。
实际上讨论这个意识的“剪切”和“复制”问题的科幻作品,已经有非常杰出的例子:科幻恐怖游戏 SOMA。

SOMA游戏界面
在这个游戏之中,主角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加拿大青年,然而在他参加了一个超先进的大脑扫描机器试验之后,他发现自己在一个未来的不知名的冰冷的实验室中醒来。在他探索的过程之中,他慢慢的发现了真相:自己只是一个意识的复制体。
到了最后他想要逃离这个即将毁灭的基地,千辛万苦将自己上传到卫星上,才再次意识到了那个从一开始实际上就已经向他揭露的讽刺的真相:意识的上传是复制而非剪切。他的另一个意识复制体幸福的活在了卫星上运行的数字世界之中,然而他的本体仍然卡在了这个即将毁灭的基地里,只能一同接受毁灭的终结。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发问,请问作者你是哪一派呢?你是支持“数字生命计划”还是支持“流浪地球计划”呢?我的答案是:跟大刘一样,我是飞船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果壳 (ID:Guokr42),作者:邓思渊,编辑:卧虫、沈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