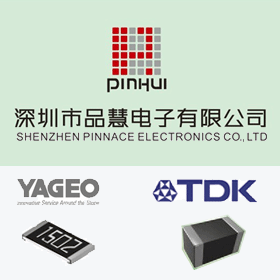一个拒绝所有“最佳xx女性”奖项的女科学家
原标题:发明激素测定方法却放弃专利,获诺奖后,她还要成为世界最佳
罗莎琳·萨斯曼·耶洛(Rosalyn Sussman Yalow),一个美国出生的犹太女孩走上物理之路,并投身于核医学领域。她与合作者找出了2型糖尿病真正的病因,并受此启发创立了放射免疫分析法,这项创举使精准测量体内微量物质成为可能,后来广泛应用于医学领域。罗莎琳因此获得了197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正如那个时代稀少的其他女科学家一样,罗莎琳的科研旅途并不平坦,但她从未放弃,不畏困难;她所追求的,是所有人中的最佳,而不仅仅是女性群体。
“望远镜带我们了解天空;显微镜为我们打开微生物世界;而放射性同位素方法论,以放射免疫分析法(RIA)为例,在科学和医学领域为人类开辟出了崭新前景。”
——罗莎琳·萨斯曼·耶洛
撰文 | 维罗妮卡
1977年冬日,罗莎琳·萨斯曼·耶洛 (Rosalyn Sussman Yalow, 1921~2011) 作为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受邀出席瑞典的颁奖晚宴。她的丈夫亚伦·耶洛 (Aaron Yalow) 作为家属一同出席,与她分坐在晚宴长桌的两侧。
负责引领罗莎琳上台的是一名年轻学生,他手中的座位表写有两位耶洛博士 (Dr. Yalow) 。学生径直走向亚伦,自信地站在他身后,认为这位便是即将上台发言的耶洛博士。罗莎琳看到这一幕,爽朗地笑出声来。她大方地起身,缓缓走向长桌的一端。学生闹了个大红脸,在一众名流的小声哄笑中,快步走向长桌尽头,与对侧的罗莎琳汇合。罗莎琳友好地与他握手,轻声安抚不知所措的年轻学生,并跟随他走向了演讲台。
图1. 1977年12月10日,罗莎琳·耶洛在诺贝尔颁奖晚宴上,身旁坐着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Carl XVI Gustaf)。| 图源:William A. Bauman and Benjamin Yalow(罗莎琳之子)
这则轶事是罗莎琳·耶洛多重身份的缩影:兢兢业业的科学研究者、关心学生的导师、科学舞台上的发言人,以及两个孩子的母亲。从不受重视的女学生到名扬天下的诺奖得主,罗莎琳的科研之路崎岖坎坷。但她向来目标明确,从不向困难屈服。只要下定决心,便将全力以赴,做到尽善尽美。
她是野心勃勃的玫瑰,即使扎根于贫瘠的土壤,也要将枝桠伸至天际。
成为小学老师,还是物理学家?
罗莎琳家族中的数位女性,皆有一身“反骨”。外祖母贝尔莎 (Bertha) 出生于显赫的德国上流家庭,却违抗家族命令,嫁给一名商人,并随之来到美国。在贝尔莎的6个孩子当中,克拉拉 (Clara) ——也就是罗莎琳的母亲——是最叛逆的一个。克拉拉的聪颖、坚强与其母亲如出一辙,选择的伴侣也同样是个勤奋踏实的商人,名为西蒙·萨斯曼 (Simon Sussman) 。
萨斯曼夫妇组成了一个典型的犹太家庭,定居于素有“东欧移民的大熔炉”之称的美国纽约城曼哈顿下东区,并在1921年迎来了他们的女儿罗莎琳·萨斯曼。罗莎琳执着坚定,自信且无畏,被她的兄长戏称为“蜂后” (The Queen Bee) 。
虽然萨斯曼夫妇未曾读过高中,但他们的两个孩子有出众的学习天分。罗莎琳进入亨特学院 (Hunter College,现纽约城市大学) 就读,这是纽约市教育系统中一所专为女子而设、学费全免的学院。她在数学和化学学科上表现出色,而在学校物理教授赫伯特·奥迪斯 (Herbert N. Otis) 和杜安·罗勒 (Duane Roller) 的影响下,罗莎琳对物理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物理学,尤其是核物理学,是时下最热门的研究领域。按照罗莎琳的话说,“似乎每一项重大实验的产出都伴随着一个诺贝尔奖。”玛丽·居里 (Marie Curie, 1867~1943) 的自传一经问世,罗莎琳便将其奉为珍宝,认为它是“有抱负的年轻女科学家们的必读书目”。在1939年1月,恩利克·费米 (Enrico Fermi, 1901~1954) 在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 举办了一场以核裂变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这引发了有关核战争的恐惧与忧虑,也同时为放射性同位素在医学研究中的应用打开了广阔空间。罗莎琳参加了这场研讨会,被费米的演说深深感染,从此在内心埋下了研究放射性同位素的火种。
1940年是罗莎琳在亨特学院度过的最后一年,她开始谋划未来的道路。罗莎琳怀着满腔的热情,想在核物理领域继续深造,但父母希望她从实际出发,安分地当一名小学老师。毕竟在当时,一个犹太女学生想要入选不错的研究生项目并获得经济支持,好似天方夜谭。果不其然,罗莎琳申请的学校接连发来拒信。
在焦头烂额之际,亨特学院的物理学教授杰罗尔德·撒迦利亚 (Jerrold Zacharias, 1905~1986) 伸出援手,将她推荐给了哥伦比亚大学内科和外科医生学院 (Columbia University’s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的鲁道夫·舍恩海默 (Rudolf Schoenheimer, 1898~1941) 教授当秘书。罗莎琳接受了这份兼职工作,为此不得不学习速记,但也获得了旁听研究生课程的机会。1941年1月,罗莎琳正式从亨特学院毕业,成为该校物理学专业的首位毕业生。
1941年2月,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UIUC) 物理系向罗莎琳伸出了橄榄枝,愿意为她免除学费,并提供每月70美元的助教薪资。罗莎琳喜出望外,这是她申请的学校中最具声望的一所。她快乐地撕掉了速记本,在当年9月正式步入物理学殿堂。罗莎琳始终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致使大量男性劳动力应征入伍,才让她获得了宝贵的求学机会。但当时美国尚未正式加入战争,她也是工学院400名教职工中唯一的女性。事实上,罗莎琳是该院自1917年以来的首位女性成员。
踏上核医学之路
在入学首日,罗莎琳与同班同学亚伦·耶洛相识。同样出身于犹太家庭的他们逐渐彼此吸引,并在两年后缔结了婚姻。由于亨特学院在1940年9月才开设物理学课程,与班里同学相比,罗莎琳的物理基础较为薄弱,她不得不加倍努力以弥补差距。在入学前的夏天,罗莎琳专程前往纽约大学 (New York University) 学习了两门物理学暑期课程。在入学第一年,除三门研究生课程外,罗莎琳额外旁听了两门本科生课程,还为做好助教工作而专程观摩一位明星讲师的课堂。
图2. 20世纪40年代的罗莎琳·耶洛和亚伦·耶洛。| 图源:Benjamin Yalow(罗莎琳之子)
即使日程繁忙,罗莎琳依旧表现优异:她的两门课程拿到全A,另一门光学课程的理论部分拿了A,而实验部分拿到A-。但物理系主任却对此表示:“这个A-证明了女性不能胜任实验工作。”骄傲的罗莎琳没有放在心上,依旧执着坚定地追求物理学真理。她夜以继日地在实验室里沉迷研究,学习制作及使用测量放射性物质的仪器。1942年,她获得硕士学位;不到三年,1945年2月她获得核物理博士学位,比其他同学提早了一整个学期。
当年UIUC录取罗莎琳的前提条件,便是不负责提供毕业后的教职。罗莎琳毕业时,二战仍未结束,没有大学愿意给一名犹太女性提供教职。她回到纽约市,在联邦电信实验室 (Federal Telecommunications Laboratory) 担任助理工程师,隶属于欧洲公司IT&T。1945年9月,亚伦博士毕业,来到纽约布朗克斯的蒙蒂菲奥里医院 (Montefiore Hospital) 的医学物理部门工作。
二战结束后,IT&T研究团队迁至欧洲,罗莎琳回到母校亨特学院担任临时副教授,但这份教学工作无法帮助她实现科研追求。彼时,核医学正在兴起,需要大量会制备和处理放射性同位素的核物理学家。通过丈夫的引荐,罗莎琳得以认识医学物理学家伊迪丝·昆比 (Edith Quimby, 1891~1982) ,昆比被认为是核医学创始人之一。罗莎琳来到昆比的实验室参观学习,凭借出众的分析和学习能力,罗莎琳很快掌握了临床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
一天,昆比接到了布朗克斯退伍军人管理医院 (Bronx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Hospital, VA Hospital) 放疗科主任伯纳德·洛斯威特 (Bernard Roswit,1910~2001) 的电话,寻求有关开展临床放射性同位素工作的建议。昆比带罗莎琳去见了她的老板焦阿基诺·菲尔拉 (Gioacchino Failla,1891~1961) 。经过短暂的交谈,菲尔拉对罗莎琳大为赞赏。他拨通洛斯威特的电话:“老伙计,听说你想要开展放射性同位素工作,我这儿有个你不能错过的人。”
1947年12月,罗莎琳应邀来到VA医院,担任放射性同位素中心的兼职顾问。起初,这里只是个看门人的房间,狭小简陋。依靠退伍军人项目提供的小笔资金和一腔热情,罗莎琳与同事们很快将其发展完善。除为医院生产放射性同位素以外,罗莎琳也和洛斯威特等医生合作发表了8篇相关论文。
图3. 罗莎琳在VA医院的实验室中认真工作。| 图源:Benjamin Yalow(罗莎琳之子)
1950年1月,罗莎琳从亨特学院辞职,全职加入VA医院。随后不久,担任她直属上司的医生便辞职了。罗莎琳的能力得到了洛斯威特的认可,因而被允许自主选择替代的医生。在搜寻的过程中,罗莎琳与所罗门·伯森医生 (Solomon Berson, 1918~1972) 一拍即合,由此开始了长达22年的合作。
“在交谈半小时以后,我就确定他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罗莎琳在多年以后如是说道。
天衣无缝的合作拍档,共创诺奖成果
罗莎琳是核物理学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医学教育,而伯森是生理学、解剖学和临床医学硕士。他们在专业知识上互补,彼此倾囊相授并互相监督,以最严格的方式训练对方。他们的办公桌相对放置,便于随时交流想法。两人都思维敏捷,能完美跟上对方的节奏,一对最佳科研拍档由此诞生。伯森名义上是罗莎琳的上司,但从1951年7月发表第一篇论文以来,他一直坚持以实际贡献决定论文署名的公平原则。在他们合作发表的数十篇论文中,有时伯森是第一作者,有时则是罗莎琳。
二人合作开展的首个研究,是运用放射性同位素估测循环血量 (circulating blood volume) ,他们的研究成果比早期的测量方法精确得多。
在此之后,他们用131I标记白蛋白及其他血清蛋白,以研究不同蛋白合成、降解及清除的速率。同时,两人还将目光转向了甲状腺功能研究。彼时,临床常用的甲亢和甲减诊断方法是让患者口服131I,但耗时长达数天,结果也不够准确。罗莎琳自主设计了检测甲状腺放射性的仪器[5],与伯森一同将131I注入患者静脉,以测量甲状腺对碘的吸收情况和血浆清除率。他们发明的测量方法仅耗时35分钟,且测量结果不受外部因素影响,论文一经问世便被盛赞为“对放射性同位素示踪诊断法最重要的贡献”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problem of diagnostic tracer procedures) 。
图4. 由罗莎琳设计的可测量患者甲状腺放射性强度的仪器。| 图源: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Clinical Investigation
1954年,伯森升任联邦退伍军人医疗系统中首个独立的放射性同位素中心的主任。在为VA医院提供临床核医学服务以外,伯森和罗莎琳对于研究方向拥有绝对的自主权。尽管资金非常有限,仅来源于微薄的部门预算和退伍军人医疗研究计划,他们依然产出了辉煌的研究成果。在深入研究甲状腺功能的同时,罗莎琳和伯森对胰岛素的兴趣也与日俱增。
选择胰岛素,有部分个人原因。罗莎琳的丈夫亚伦在12岁时便确诊1型糖尿病,需要每日注射胰岛素。更重要的是,糖尿病是继甲亢和甲减之后发病率最高的内分泌疾病,但胰岛素的代谢过程仍充满未知。在当时的认知中,1型糖尿病以胰腺产生的胰岛素不足为特征;而在2型糖尿病中,胰岛β细胞功能正常,患者血糖升高的原因成谜。1952年,亚瑟·米尔斯基 (Arthur Mirsky, 1907~1974) 提出假设,认为2型糖尿病患者的肝脏中可能存在胰岛素酶,造成患者体内胰岛素减少速率高于正常值。
为验证米尔斯基的假设,罗莎琳和伯森将131I标记的胰岛素注射入糖尿病和非糖尿病患者体内,在数小时后收集患者血液样本,测量放射性强度。意料之外的是,糖尿病患者血液中胰岛素存在时间比非糖尿病患者的对照组更长。他们还注意到,在从未接受过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患者中,胰岛素减少速率与对照组相同。
所以,2型糖尿病的致病原因并不在于患者体内胰岛素的含量,那是因为什么?在重复的电泳、离心和沉淀之后,他们发现接受胰岛素治疗的患者体内,131I标记的胰岛素并非游离态,而是与γ-球蛋白相结合。罗莎琳和伯森敏锐地意识到,这极有可能是一种抗体。与抗体的结合延长了胰岛素在患者体内的半衰期,也阻碍了胰岛素对血糖的调控。
图5. 在接受过或未接受过胰岛素治疗的患者中经静脉注射131I标记胰岛素后,放射性强度随时间变化曲线。曲线MN2为患者接受为期4个月的胰岛素治疗后,曲线MN1为胰岛素治疗以前。图中可见MN2的放射性强度(胰岛素含量)下降速率明显低于MN1。| 图源:Rosalyn Yalow’s Nobel Lecture
罗莎琳和伯森撰写了一篇20页的论文,投稿至《临床研究杂志》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JCI) ,却收到了拒信。在多年以后的诺贝尔奖致辞上,罗莎琳还自豪地向观众展示了这封拒信。审稿人和杂志编辑认为,像胰岛素这么小的蛋白质不具有免疫原性,无法让人体产生抗体。彼时,证明抗体存在的唯一方式是观察到抗原-抗体复合物形成的沉淀,大部分人认为可溶性抗原-抗体复合物并不存在。在编辑的要求下,罗莎琳和伯森作出妥协,将标题中的“抗体”替换为“球蛋白”,才换来了1956年的论文出版。
罗莎琳和伯森揭示了2型糖尿病的真正病因——胰岛素抵抗,而非胰岛素不足。由此,2型糖尿病的治疗策略也得到纠正。论文出版之后,很快在多方的重复实验中得到认证,在免疫学和糖尿病治疗领域掀起波澜。人们意识到,为了避免抗体产生,糖尿病患者不能注射以往常用的猪、牛胰岛素,应改用人源性胰岛素。现如今,批量生产的胰岛素经基因工程的编辑,已做到与人源性胰岛素完全一致。
图6. 1957年,美国糖尿病协会授予罗莎琳·耶洛和所罗门·伯森礼来奖(Eli Lilly Award),此为二人获奖后的合影。这是二人组合斩获的第一个奖项,此后各类奖项纷至沓来。| 图源:Benjamin Yalow(罗莎琳之子)
在讨论胰岛素抗体的这篇论文中,罗莎琳和伯森还报告了一个意外发现:在抗体浓度确定时,131I标记胰岛素与抗体的结合率与体系中胰岛素的总量呈函数关系。他们意识到,通过逆转实验过程,也许可以测量患者血液中胰岛素的含量。其后的三年里,罗莎琳和伯森致力于研发测量胰岛素含量的可行方法。他们优化了抗体制备条件,发现豚鼠是最佳实验生物。每天早晨,罗莎琳会将豚鼠从笼子里取出,逐个拥抱和安抚,因为她相信幸福的动物才能产出优质抗体。经过大量实验和复杂计算,他们得出了胰岛素与抗体结合反应的平衡常数 (equilibrium constant) 和结合亲和力 (binding affinity) 。
1960年,罗莎琳和伯森发表了他们突破性的实验成果:无需将患者暴露在核辐射下,仅需抽取一管血样,便可测定体内胰岛素含量。实验过程其实相当简单。在含有一定浓度胰岛素抗体和131I标记胰岛素的体系中,加入不同总量的无标记胰岛素,无标记胰岛素便会与131I标记胰岛素相互竞争,使得部分131I标记胰岛素从结合态(B)变为游离态(F)。通过测定加入不同总量无标记胰岛素时,B与F的放射性强度之比,便可建立标准曲线。实际为患者测量时就相当于逆过程,在患者血样中加入指定浓度的抗体和131I标记胰岛素,测量B/F值并对照标准曲线,即可得出胰岛素含量。
图7. RIA的基础原理图示:带放射性同位素标记抗原和无标记抗原与特异性抗体结合的竞争性反应。| 图源:Rosalyn Yalow’s Nobel Lecture
罗莎琳和伯森的测量方法被称为放射免疫分析法 (radioimmunoassay, RIA) ,后续在医学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也为罗莎琳赢得了1977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一半,获奖理由是“发明肽激素的放射免疫分析法”。遗憾的是,1972年4月,伯森因心脏病发作不幸离世,与诺奖失之交臂。那一年诺奖的另一半由罗杰·吉尔曼 (Roger Guillemin, 1924~) 和安德鲁·沙利 (Andrew Schally, 1926~) 共同分享,他们运用RIA发现和分离了下丘脑-垂体轴中的多种肽激素。
图8. 197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名单。| 图源:nobelprize.org
真正改变世界的发现,不需要专利
放射免疫分析法 (RIA) 是一项灵敏度极高的技术,可以测得10-40~10-42 M浓度的物质,相当于在90立方公里的水域中检测加入的一茶匙糖。借助RIA,能快速准确地测量激素、酶、维生素、病毒、药物和数百种其他物质的浓度,许多疾病的诊断、治疗或检测成为可能。例如RIA广泛应用于内分泌领域,使得甲状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更加精准便捷,患有侏儒症的儿童可及早筛出并补充生长激素,不孕不育症相关的性激素功能障碍也便于诊出……
通过RIA,罗莎琳与同事发现除消化系统以外,大脑 (尤其是大脑皮层) 中也会产生内源性胆囊收缩素 (cholecystokinin, CCK) ,由此,神经递质 (neurotransmitter) 的概念和内涵得以拓宽。此后,许多其他的胃肠肽激素,如生长抑素 (somatostatin) 、P物质 (substance P) 和血管活性肠肽 (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 等也被证实存在于大脑中。下丘脑-垂体轴中的多种肽激素的发现与分离,包括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 (thyr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TRH) 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GnRH) ,也是基于RIA的应用。RIA实际上开启了一门新的科学——神经内分泌学 (neuroendocrinology) ,研究大脑中与控制内分泌系统相关的化学信使。
虽然罗莎琳凭借RIA在内分泌领域的应用斩获诺奖,但RIA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临床基础研究工具之一,实际应用范围远不止于此。罗莎琳实验室成员约翰·沃尔什 (John Walsh) 开发了首个针对病毒的RIA分析,使得对血库用血进行常规筛查成为可能,极大地预防了肝炎病毒的传播。针对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 (purified protein derivative, PPD) 设计的RIA,可用于结核分枝杆菌的诊断和监测。RIA还可用于对运动员进行违禁药物测试;能够直接检测酶的含量,而非依赖于间接的催化反应效果;如今实验室常用的酶联免疫吸附剂测定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也是在RIA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RIA可能的用途清单无穷无尽,也带来了潜在的巨大利润。但罗莎琳和伯森始终坚持不申请专利,而是致力于推广它的应用。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来到他们的实验室接受培训,临走时还会获赠一瓶珍贵的自制抗体。RIA便捷、安全、成本低廉,即使是在经济不发达、医疗落后的地区,也得到了广泛应用。罗莎琳在诺奖获奖感言的结尾处感慨道:“望远镜带我们了解天空;显微镜为我们打开微生物世界;而放射性同位素方法论,以RIA为例,在科学和医学领域为人类开辟出了崭新前景。” (The first telescope opened the heavens; the first microscope opened the world of the microbes; radioisotopic methodology, as exemplified by RIA, has shown the potential for opening new vistas in science and medicine. )
诺奖得主的豪言,科研生子两不误
1972年,伯森的离世让罗莎琳备受打击,但她努力走出了阴霾,继续在科研之路上执着求索。
在此之前,擅长社交、口才绝佳的伯森撰写了大部分论文的初稿,并总是作为他们中的发言人上台致辞。许多人因此认为,伯森是二人组合中的“大脑”,而罗莎琳只是负责执行的“肌肉”。伯森离世后,罗莎琳则用实际行动驳斥了流言:她成为实验室的负责人,带领实验室成员在五年内发表了多达60篇论文,并在各类学术会议中上台发言,核医学女科学家的形象给学术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罗莎琳的要求下,实验室更名为所罗门·伯森实验室。在此后所有罗莎琳发表的论文中,伯森之名都出现在实验室名称处,与她的名字一同列于首页。这是她对挚友的怀念,也是对伯森科研成就的认可和尊重。
1975年,罗莎琳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院士。第二年,她成为获得阿尔伯特·拉斯克医学研究奖 (Albert Lasker Basic Medical Science Award) 的首位女性及首位核物理学家。1977年10月13日清晨6点45分,来自瑞典的电话铃声响起时,罗莎琳已来到实验室开启一天的工作。
图9. 1977年10月13日,在实验室中刚刚接到诺贝尔奖获奖电话的罗莎琳·耶洛。| 图源:Wikipedia
罗莎琳·耶洛是历史上第二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女性,第一位是盖蒂·科里 (Gerty Cori, 1896~1957) ,因发现糖代谢的酶促反应,与丈夫卡尔·科里 (Carl Cori, 1896~1984) 分享了1947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正如罗莎琳把居里夫人视为偶像一般,许多年轻女科学家也将罗莎琳视为楷模。但罗莎琳本人,并不是改善女性在科研中的待遇的拥护者。
图10. 罗莎琳与丈夫和孩子们的合影。从左至右分别是本杰明·耶洛(Benjamin Yalow)、亚伦·耶洛、罗莎琳·耶洛和伊莱娜·耶洛(Elanna Yalow)。| 图源:Benjamin Yalow(罗莎琳之子)
在沉浸于RIA的研发和应用的同时,罗莎琳还养育了两个孩子。退伍军人医疗体系规定,妇女怀孕达五个月时,必须辞职且不能再返岗。罗莎琳无视了这条规定,直到生产前一天还在实验室工作。产后一周,她便马不停蹄地重新投入工作。两年后,她生育了第二个孩子。受传统观点影响,罗莎琳认为打理家庭是妻子的天职。每天清晨,她早起去实验室工作,中途回家准备早餐和送孩子上学。她趁实验间隙回家烹饪午饭和晚饭,饭后再返回实验室,工作至深夜。
罗莎琳对自己极为严苛,对待其他女科学家亦然。她坚持女性应兼顾事业和家庭,对为事业放弃生育的同行持批判态度,并认为女权运动是对她传统信仰的挑战。尽管如此,罗莎琳用实际行动为女性在科学界开辟出了新的道路,并积极鼓励女学生追求科学事业。她影响了众多女性,其中最著名的是米尔德雷德·德雷斯尔豪斯 (Mildred Dresselhaus, 1930~2017) :在罗莎琳的引导下,未来的“碳科学女王”离开小学教学,开启科研生涯。
罗莎琳曾对女性科研工作者们说:“我们必须相信自己;必须拥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来实现我们的远大抱负;我们之中有幸作出成就的那部分人,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担当后来者的榜样,并为她们提供实用建议。我们需要的,不是反向歧视,而是机会平等——让我们之中渴望摘星星的人,拥有伸手触及的可能。”
罗莎琳这一生,骄傲坚强,从不畏惧困难,也不屑于藏匿野心。她拒绝了所有名为“最佳xx女性”的奖项,因为她所追求的,是所有人中的最佳,而非仅限于女性群体。罗莎琳办公室的墙上,写着这样的话语:“无论女人做什么,她们必须做得比男人好一倍,才会被认为有他们一半好。所幸的是,这并不难。” (Whatever women do they must do twice as well as men to be thought half as good. Luckily, this is not diffic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