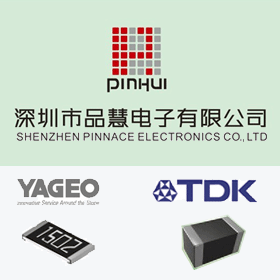关于美国科技巨头的神话和现实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互联网怪盗团 (ID:TMTphantom),作者:怪盗团团长裴培,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0年以来,在国内舆论界和投资界存在一种迷思:中美两国的互联网巨头不是同一个物种。前者聚焦于低层次的流量变现,后者则致力于高智力的科技竞争;前者只能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市场称王称霸,后者则可以以美国为基地收割全世界;前者心胸狭窄、总是惦记着与小型线下零售商争利,后者则心胸宽阔,一心想扩展人类活动的边疆。
因此,中国的互联网巨头被开除了“科技籍”,只能被称为“流量平台”;美国的互联网巨头则可以独享“科技巨头”这个称谓。很多人感叹,中国互联网公司只会从实体经济吸血,不像美国互联网公司能够进行硬科技创新。有些人更不客气地认为,其实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互联网公司的贪婪和无能。
上面这些迷思,固然不是毫无道理,却与真相相去甚远,尤其是误解了美国的互联网行业。严格地说,国内对于美国互联网公司的研究一直不够充分,无论从投资的角度、业务的角度还是科技的角度而言都是如此。就连一些严肃的研究机构,也主要是使用中文翻译的二手信息,加上一些不太正规的消息渠道,得出一大堆似是而非的结论。其实,它们的本意可能也不是研究美国互联网行业,而是为了给攻击中国互联网行业寻找“背景板”而已。
本研究报告的目的,就是全面深入地研究美国最大的几家科技巨头的业务、财务和战略,理解它们做过什么、在做什么、想做什么;在此基础之上,对中国的对应公司进行严肃的对比分析。我相信,比起那些观点先行、指桑骂槐式的“研究”,我们更需要这种事实先行、基于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
幸运的是,关于美国科技巨头的公开资料非常丰富。公司财报、管理层电话会议纪要是每个季度公布的;公司出席大型投资者交流会的发言一般也是公开的;欧美的咨询公司、行业研究机构发布了大量的行业统计和估算;美国科技媒体的报道数量极多,尽管我们需要辨别其可信度。本研究所援引的各种数据,均已予以注明,并向原始资料方致以诚挚的谢意。
美国科技巨头:以MAGA为核心的研究
美国科技巨头的主流商业模式:以2C为核心,扩张至2B及“硬科技”
Microsoft vs. Amazon: 不同出发点的殊途同归
Google vs. IBM: 硬科技的核心问题在于应用场景
美国科技巨头也惦记着本地零售,而且力争将其作为突破口
美国的科技反垄断:雷声很大,雨点好像比较小
2021年底,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绿色为“科技巨头”
美国科技巨头:以MAGA为核心的研究
“科技巨头”(Big Tech)这个词,在英语中流行的时间并不长。2016-17年,随着美国国会展开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问题的调查,Facebook因为其对社交媒体的巨大影响力而被媒体加上了“科技巨头”的头衔。
2017年11月,彭博的一篇文章将Apple、Alphabet (Google)、Facebook、Microsoft和Amazon合称为“五巨头”(Big Five),认为它们能够主宰美国经济。2017年《纽约时报》年度推荐图书《没有思想的世界:科技巨头的存在主义威胁》(World without Mind: The Existential Threat of Big Tech)将Apple、Facebook、Google、Amazon视为彻底控制人类知识和信息的“四巨头”(Big Four)。2020年,上述“四巨头”的CEO均出席了众议院的反垄断调查听证会。
在近年来的美国,关于限制或拆分科技巨头的倡议不绝于耳,但是行动尚未产生。在可见的未来,上述四巨头或五巨头仍将是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主宰力量。我们的研究也将主要围绕着它们进行。
从FANG到MAGA:科技巨头定义的演变
2013年,知名投资者和电视嘉宾Jim Cramer提出了FANG (Facebook, Amazon, Netflix, Google)组合,建议每个投资者都应买入这些“彻底主宰了市场的公司”。2017年,Cramer又加入了Apple,从而形成了FAANG“五巨头”的概念。这一概念在中国流传很广,至今在百度上仍能搜到632万条中文页面;腾讯、阿里等中国互联网公司,以及一些科创板上市公司,都曾被券商或媒体称为“中国FAANG”。
然而,随着Netflix的掉队以及Microsoft的强势兴起,FAANG这个组合也过时了。2020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Donald Trump提出了MAGA (Microsoft,Apple,Google,Amazon)组合,它们均突破了1万亿美元市值大关,被Trump认为承载了“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的使命。Facebook由于市值没有达到1万亿美元,而被排除在此组合之外。
2021年9月,Facebook在更名Meta Platforms之后,市值终于突破了1万亿美元(尽管只是昙花一现)。Jim Cramer随即抛弃了FAANG概念,转而提出MAMAA (Microsoft,Apple,Meta,Amazon,Alphabet)组合。不过,鉴于MAMAA这个缩写非常拗口,很多人还是习惯使用MAGA;其中的M既代表Microsoft, 也代表Meta。
截止2022年4月,科技巨头对美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统治仍很稳固。MAGA全部进入了美国市值最大的十家公司之列——其中Apple和Microsoft的市值超过了2万亿美元,Alphabet和Amazon超过了1万亿美元,只有Meta明显掉队;作为一个整体,它们占据了美国股市总市值的40%以上。
在美国市值前十名的公司中,还存在Tesla和Nvidia这两家科技含量较高、偶尔会被人拿来与“科技巨头”做对比的公司。其中,Tesla的创始人Elon Musk最早就是做网络支付起家,迄今还与信息科技行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Nvidia的芯片则为互联网娱乐内容及Web3.0提供了基础支持。
然而,正如上文提到的:美国立法者和媒体对“科技巨头”的定义,不仅在于其科技创新性,还在于其对经济的主宰性,以及对人类知识和信息的控制性。Tesla和Nvidia目前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主宰性”和“控制性”,对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也尚没有MAGA那样高,也没有被纳入美国国会的反垄断调查对象。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对象,仍然是MAGA (Microsoft,Meta,Apple,Google/Alphabet,Amazon)这“五巨头”。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用户规模庞大,掌握了复杂且敏感的数据,对经济活动和社会舆论有较强的影响力(无论它们想不想发挥这种影响力)。Tesla不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Nvidia不直接掌握复杂的数据,所以与“五巨头”有显著区别;Netflix的用户规模和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力明显差了一个档次,其他美国互联网公司就更差了,所以也不能与“五巨头”放在一个框架下研究。
在不考虑科技领域出现颠覆性创新的情况下,上述五巨头当中有四个的统治力都很稳固,仅Meta一家有坠落的风险——这就是Meta为何在元宇宙方面投入大量资源,企图打开新的增长点的原因。但是,Meta的市值和收入规模仍然比五巨头之外的其他任何美国互联网公司高一大截,即便真的坠落,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发生的。至少在未来2-3年内,MAGA或“五巨头”的概念仍然将伴随我们。
以消费业务为核心增长点的美国科技巨头
在中国,最成功的科技公司大部分是消费互联网公司,在美国也不例外。事实上,MAGA之所以被认为“主宰经济、控制了人类知识”,主要是由于它们对消费者提供着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无孔不入地介入了大众生活的每个环节。在五巨头之中,有四个是以消费业务为主要收入和利润来源的,仅有Microsoft例外。
Apple的业务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大类,即iPhone/iPad/Mac/可穿戴设备等“消费电子产品”,以及用户增值服务。毫无疑问,它们都是消费业务。虽然企业和机构客户也经常从Apple进行采购,但它们对Apple而言无非是大一点的“消费者”而已。Apple没有自己的公有云服务,就连iCloud也是基于Amazon等第三方提供的基础设施。或许我们可以勉强把Apple的工作站和专业视频、设计软件称为“企业级产品”,可是即便如此,它们创造的收入比例很低。
可能有人会争辩说,Apple是“智能硬件公司”而不是“消费互联网公司”。这个争辩毫无意义,因为Apple产品最大的优势不是配置或设计,而是基于iOS/Mac OS的生态系统。阻止Apple用户改投安卓阵营的最大力量,是它的硬件、软件、服务一体化能力。从这个角度讲,Apple既是智能硬件的极致,也是消费互联网的极致。
Meta的几乎全部收入都来自“Meta App家族”(包括Facebook, Instagram, WhatsApp等)的广告,这些App也全是消费应用,无一例外。近年来,Meta大举押注VR业务(按照更时髦的名词是“元宇宙”),但它生产的VR硬件迄今主要还是卖给消费者的。Mark Zuckerberg曾多次表达希望把元宇宙带到办公场景的愿景,可惜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实现。
2022年2月,Meta管理层在财报电话会议上提出了新的一年的七个“优先投资方向”:短视频、社群通信、电商、广告、用户隐私、AI和元宇宙——几乎全部面向消费端。Meta在新技术、新产品上进行投入的根本目的,仍然是增加广告位、提高广告效率和报价。或许等到元宇宙普及之后,Meta会发生变化,但现在它还是纯粹的消费互联网公司。
Alphabet的主营业务分为Google服务、Google云和“其他尝试”,前者是以广告为主的消费业务,贡献了95%的收入;Google云是企业业务,贡献了5%的收入。由于Google云和“其他尝试”一直在亏损,消费业务对Alphabet营业利润的贡献比例超过了100%。2021年下半年,Alphabet的强劲增长主要是源于电商、线下零售等行业广告开支的增长。
Google云近年来的营业亏损在不断缩小,但其规模比起AWS (Amazon)和Azure (Microsoft)还是要差一大截。由于Google既缺乏企业软件业务,又缺乏规模效应,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对云计算市场的领导地位发起挑战。至于Alphabet旗下的“其他尝试”,迄今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它在可见的未来仍将是比较纯粹的消费互联网公司。
Amazon的收入有87%来自电商平台等消费互联网业务,13%来自AWS云服务。AWS一直是Amazon最大的利润来源,有些季度(例如2021年第四季度)甚至能贡献全部营业利润。相比之下,亚马逊的北美电商业务一直处于微利状态,而国际电商业务大部分时候还在亏钱。考虑到AWS的规模效应和技术优势,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是Amazon的主要利润来源。
有人认为,Amazon的经营策略就是用赚钱的企业云服务去补贴不赚钱的电商业务,这个观点并不全面。因为在Amazon的电商业务中,第三方商家业务(包括佣金、配送收费和广告)是盈利的,而且盈利规模可能超过了AWS;自营业务则是亏损的。准确地说,Amazon是在用第三方商家和企业云服务同时补贴自营电商,它是一家横跨消费和企业业务、以消费互联网为主的公司。
Microsoft是五巨头当中唯一一家以企业客户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公司。它将自己的业务划分为“生产力和商业流程”“智能云”“其他个人计算”三大板块,其中最后一项主要是消费业务,上个季度贡献了34%的收入和29%的营业利润。对动视暴雪的收购,将大幅加强Microsoft的自研游戏内容,从而提升消费业务的占比。
在历史上,Microsoft一直在努力进军消费市场:1999年发布Xbox游戏主机,2006年推出Zune音乐播放器,2009年推出Bing搜索引擎,2011年收购Skype,2016年收购LinkedIn;在此期间,Microsoft还在游戏内容方面投入了数百亿美元。虽然这些努力经常失败,但它从未放弃。收购动视暴雪,代表着Microsoft加码消费业务、在企业和消费两个领域均成为顶尖公司的决心。
事实证明,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收入和市值规模最大的公司一般都是以消费业务(ToC)为主;只服务企业客户(To B)的公司很难成为顶尖巨头。除了Microsoft这一个异数之外,Cisco、Orcale、Accenture、Salesforce.com等以企业服务为主的美国科技公司的市值,均只能达到2000亿美元左右。
哪怕我们把目光从科技行业移开,放眼更广阔的领域,结论也不会有变化——1.09万亿美元市值的Tesla是一家高端消费品(家用汽车)公司;6000亿美元市值的Nvidia,同时向企业和个人客户提供显卡;4300亿美元市值的Walmart是美国除了Amazon之外最大的零售商。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其实很好理解:一个伟大的发明创造、一个优秀的商业模式,总要进入千家万户,才能真正改变人类社会的面貌。而且,一个国家越是发达,消费对经济的贡献比例就越高,消费者也就越乐意为优质产品和服务买单。大部分新兴行业的成长历程,就是火炬从企业服务(To B)型公司逐渐传递到消费者服务(To C)型公司的历程。信息科技行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火炬从IBM这样典型的企业服务商手中,传递到Microsoft这样横跨企业和消费业务的公司手中,再传递到Apple和Alphabet这样典型的消费互联网平台手中。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To B业务对科技巨头没有价值。首先,这仍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增速不慢,足以提供大量的收入和利润。其次,To B和To C之间往往能产生协同效应,最经典的例子就是Amazon在电商基础设施之上发展出了云计算。最后,许多新技术、新业态可以在企业服务市场得到验证,循序渐进地走进千家万户(包括国内所谓的“硬科技”)。下一章我们将分析美国科技巨头如何在2C和2B市场形成合力,并且进军国内资本市场非常热衷的“硬科技”业务。
美国科技巨头的发展路径:横跨To C/To B,以应用场景为“硬科技”的基础
在五巨头当中,除了Microsoft以To B业务为大本营之外,其他四家均发源于To C业务,而且迄今以To C业务为主要收入来源。其中,Amazon和Alphabet对To B的扩张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可能成为To C + To B的跨界巨头;Meta希望通过对元宇宙的研发,进军远程办公这一To B市场;只有Apple尚未对To B业务进行实质性的扩张。
上述四家公司,均在“硬科技”方面取得了突破:Amazon的芯片、无人机和机器人;Alphabet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Meta的VR硬件;以及Apple的芯片。它们的“硬科技”研发,也是以强大的消费应用场景为基础的,是需求导向而非“实验室导向”的研发。这一点,国内很多人似乎不懂或装做不懂。
Amazon: 以电商平台为基础的四面出击
Amazon的财报将其自身业务划分为三大板块:北美业务,贡献了大约60%的收入,但是基本处于微利状态(偶尔还会亏损);国际业务,贡献了25-30%的收入,盈利能力更弱,偶尔会爆出较高的亏损;AWS,收入贡献比例最小,却是唯一稳定的利润来源。事实上,AWS和Microsoft Azure可能是全球仅有的两个稳定盈利的大型公有云 (IaaS & PaaS)平台。第一眼看上去,Amazon似乎是在用赚钱的云计算去补贴亏钱的消费互联网业务,与国内的阿里巴巴、腾讯完全相反。
然而,这就是事实吗?Amazon的电商业务太复杂了,不能仅仅根据地理位置去分析。虽然Amazon早期是以自营电商为主,但是近年来第三方商家的地位越来越重要。Amazon官方没有披露过第三方GMV占比,外部研究机构一般认为第三方早已贡献了一半以上的GMV,甚至可能接近三分之二。
幸运的是,Amazon财报提供了另一种收入拆分方式,即根据收入性质(而不是地理区域)进行披露。我们可以以此为依据,粗略地将其收入重新分类如下:
自营电商,包括在线自营销售收入、线下自营销售收入,以及Amazon Prime会员收入。在这些业务中,Amazon直接将商品销售给用户,负责整个交易流程。
第三方电商,包括第三方卖家缴纳的费用,以及它们在Amazon平台的广告费。在这些业务中,Amazon扮演平台或中间人的角色。
AWS,即公有云业务,这一项没有变化。
在重新分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第三方电商为Amazon贡献了大约30%的收入,而且过去两年的复合增速快于自营电商(与AWS增速相仿)。最近几个季度,Amazon管理层不断强调要做好电商广告业务,也就是吸引第三方商家增加广告投放;由此可见,第三方电商收入比例提升的趋势应该还会继续。
Amazon没有分别披露过自营电商和第三方电商业务的利润率,但是从常理推断,后者的利润率高于前者,因为Amazon在其中承担的成本较少。2018年,Morgan Stanley分析师估计Amazon第三方电商(不含广告)的营业利润率约为20%;2020年,Wedbush分析师估计该业务的利润率已经接近AWS的水平,即30%左右——如果加上广告收入,营业利润率只会更高。
非营利研究机构ILSR (Institute for Self-Reliance)的估算是:2020年,Amazon在第三方电商业务的营业利润为240亿美元,在AWS的营业利润为135亿美元,在自营电商业务的营业亏损为150亿美元。换句话说,Amazon不是在用云计算补贴电商业务,而是在用第三方电商和云计算同时补贴自营电商业务。
自营电商、第三方电商、云计算,构成了Amazon增长飞轮的三位一体:自营电商负责提供性价比最高的特定商品,同时提升平台整体用户体验;第三方电商负责充实货架、提供多元化的商品,同时产生强劲的现金流;云计算负责开拓To B业务,同时产生一定的现金流。这三者的基础设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可复用的,例如AWS的服务器可以用于Amazon自身的电商业务,而第三方商家也可以选择Amazon配送服务(FBA)。因此,Amazon得以不断摊薄成本、扩大用户群和商品/服务范围。
2021年,Amazon的配送开支(Fulfillment Expense)高达751亿美元,是销货成本(COGS)之外最大的单项开支;同年,Amazon Prime会员付费收入仅为318亿美元。看起来,Amazon在为会员提供高质量配送服务纯属赔本赚吆喝。
然而,如果我们把第三方电商业务考虑进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根据ILSR的估算,2021年,Amazon从第三方商家收取了约500亿美元的配送费。因此,Amazon通过配送服务产生的收入应为818亿美元(318亿+500亿),足以覆盖配送开支。
值得一提的是,咨询公司eMarketer认为,2021年,亚马逊施加给第三方商家的总货币化率(包括基本佣金、配送费和广告收入)高达34%,而且这个比例已经连续上升了多年。相比之下,通过阿里巴巴财报可以推算,国内淘系电商的货币化率仅为4.2%(已扣除天猫超市等自营业务)。这个数字或许低估了淘系商家的实际负担,因为它们往往还需要为代运营商(Taobao Partner,TP)支付费用;不过,即便考虑到这一点,淘系商家的负担率还是远远低于Amazon商家。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第三方电商,即所谓“平台收租”(Toll-road)业务,是Amazon帝国版图的“奶牛”,其财务意义远超AWS。随着Microsoft Azure、Google Cloud等竞争对手的崛起,甚至有一种可能性:Amazon将主动降低AWS的利润率,采取激进的定价策略,从而维护在云计算市场的支配地位。如果这种情况成真,第三方电商的“奶牛”作用将更加凸显。
经过多年的发展,AWS已经具备了一整套软件及硬件开发能力,也通过收购具备了芯片设计能力。而Amazon的“硬科技”研发实力不仅限于此,更多地体现在电商业务中。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有:
Amazon Robotics, 原名Kiva Systems, 从事全自动仓储物流系统(机器人)的研发。2012年,Amazon以7.75亿美元收购该公司,然后停止了对外销售,让它专门为Amazon电商仓库提供机器人。截止2019年,有超过20万个机器人在Amazon仓库工作;如果没有它们,Amazon几乎不可能提供次日达服务。
Amazon Prime Air, 旨在为城市消费者提供30分钟达的无人机送货服务,所用的无人机及其系统均由Amazon自主研发。该服务于2013年开始策划,原计划于2019年开始运行,不过推迟至今尚未展开。Prime Air部门同时也负责Amazon无人驾驶和陆地无人货运系统的开发。
Zoox,同样致力于无人驾驶研发,但主要应用场景是无人出租车(Robo-taxi);2020年被Amazon以12亿美元收购。目前,该公司已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无人驾驶运输服务许可,并在美国其他地区进行测试。
从2019年起,Amazon每年举办re: Mars科技大会,主题是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自动化(Automation)、机器人(Robotics)、太空探索(Space)——这代表了Amazon在“硬科技”领域的主要探索方向,其中前三个都与电商业务息息相关。显然,Amazon对这些方向的研究,既是为了走向所谓“星辰大海”,也是为了短期的实际业务需要。
Amazon的发展历程,给想要进军To B业务和“硬科技”的互联网公司提供了宝贵经验:
首先,To C业务应当为To B业务提供现金流、种子客户和可复用的基础设施,直至后者具备独立造血能力。上述三条是AWS成为公有云市场霸主的先决条件。
其次,即使To B业务已经可以稳定盈利,在To C业务中存在“奶牛”(财务支撑)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Amazon第三方电商业务的战略意义——Microsoft和Google管理层大概对此心知肚明。
再次,“硬科技”研发要基于自身业务场景的需求,以解决业务问题为出发点。电商仓储物流似乎是一件没有技术含量的“传统”生意,可是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出的机器人技术,以及正在测试的无人机配送、陆地无人配送系统,就是不折不扣的“硬科技”。
最后,绝对的资源优势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在2012年以前,Amazon很少进行大规模收购;从2012年开始,Amazon由于主营业务发展强劲、现金流比较充裕,遂开始在新兴技术和基础研发领域进行频繁的收购。除了上文提到的Kive和Zoox, Amazon的服务器芯片设计能力也是来自收购。历史一再证明,虽然钱不是唯一的问题,但如果能解决钱的问题,其他大部分问题皆可迎刃而解。
Alphabet: 广告业务仍是唯一的核心
自从2015年进行组织架构调整以来,Google母公司(也是上市公司实体)已经改名为Alphabet,在机器人、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多个新兴领域进行内部孵化和投资。然而,直到最近一个季度,Alphabet仍有92%的收入来自Google的消费互联网服务(主要是广告),7%来自Google云服务;“其他尝试”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在利润端就更是如此了:消费互联网贡献了全部营业利润;云服务处于亏损状态,不过亏损有缩小的趋势;“其他尝试”的亏损则在不断扩大,而且营业亏损远大于营业收入。
根据Google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的解释,Alphabet有两层含义:第一是“象征语言,而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创新之一”;第二是“为超额收益所下的赌注”(Alpha-bet)。讽刺的是,迄今为止Alphabet所下的一切赌注,仅有Google是成功的。从业务和投资的层面看,研究Alphabet就意味着研究Google,仅此而已。
2021年,Google消费互联网业务同比增长了32%,其中第四季度更是同比激增了36%。如此强劲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后疫情时代”美国经济的复苏和转型。美国互动广告局(IAB)的调查显示,在疫情期间,美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加快了将广告预算转移到线上的速度;在疫情逐渐缓和之后,线上广告开支的恢复速度明显快于线下广告。
在2021年四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Alphabet管理层强调了零售行业对其广告收入的重要意义——疫情大幅提升了美国电商渗透率的提升速度,尤其是催生了一批互联网原生的DTC (Direct-to-Consumer)品牌,这些品牌的获客非常依赖于搜索广告。YouTube的广告收入也在激增,大批零售品牌都在探索基于YouTube的效果广告,乃至直播带货等更新鲜、更直接的形式。
根据eMarketer的预测,2022年美国广告开支增速最快的行业是零售,其次是快速消费品,而它们都是Google非常擅长的领域。如果疫情能够进一步缓解,促进出行需求上升,那么旅行、线下娱乐行业也可能成为Google重要的收入增长引擎。在疫情爆发前,Google已经是全世界最大、最成功的广告平台了;疫情则进一步加强了它的统治地位。
看到这里,很多中国投资者及互联网从业者肯定会产生疑问:为什么百度与Google之间的差距会拉得这么大?在中国,近年来同样出现了明显的“广告开支线上化”趋势,可是胜利果实首先被字节跳动拿走了,其次被腾讯、阿里拿走了;百度核心的搜索引擎业务被认为落后于时代、不适应移动互联网环境。为什么Google就能追上乃至引领时代?
原因很多,既有技术上的,也有战略、管理和组织效率上的。但是,最核心的原因在于应用场景:Google成功地介入了零售交易环节,包括线上电商和线下实体购物场景;它能帮助零售商(包括品牌商和分销商)高效触及用户,而百度在国内做不到这一点。因此,Google在美国和欧洲扮演的其实是“百度兼阿里”的角色,就像Amazon扮演的其实是“京东兼阿里”的角色——它们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导致在美国和欧洲不再需要一家淘宝/天猫这样的第三方电商市场平台。
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Google Shopping(最早称为Froogle, 后改名Google Product Search, 2012年改为现名)是Google旗下基于商品的付费推广服务。广告主将自己的商品详情在此注册,然后围绕商品购买关键词。对用户而言,Google Shopping不仅能够显示商品细节和价格,甚至能直接显示评价;它的推广结果永远出现在最上一列,不会与自然搜索结果混淆。由于Google Shopping促成交易的效率很高,所以能同时成为DTC品牌和传统品牌广告主的重要投放场景。
Google Maps能够为线下商户提供基于地理位置的推广服务。作为安卓平台最流行的移动APP(安装用户超过20亿人),Google Maps本来就是很多商户的重要广告投放渠道。2021年,Google推出了新的搜索功能,允许用户直接搜索店内商品,确认本地商店是否有货(In Stock),乃至预约路边自提(Curbside Pickup)。在疫情期间,由于全球供应链紧张,用户在Google对“有货状态”的搜索量一度激增。即便在疫情缓和之后,本地零售商也比以前更依赖Google推广了。
Google Shopping允许消费者直接触达商品乃至比价
Google声称,将搜索引擎和地图服务结合起来,就能向零售商提供它们梦寐以求的“全渠道零售”(Omnichannel)解决方案——所谓“全渠道零售”,就是将线下实体供应链和电商供应链进行整合,使得消费者可以在快递交付、店内交付和路边交付之间任意切换。中国消费者可能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地广人稀的美国等西方国家,这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用户体验,或许还能降低成本。
根据Google管理层的披露,2021年10月(感恩节前),在Google搜索“我附近的礼品店”的数量同比上升了60%;在Google Maps搜索“我附近的礼品”的数量同比上升了70%。看样子,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习惯于在拜访亲友之前在Google搜索本地商店,然后临时抱佛脚地购买礼品。虽然Google并不经营任何零售业务,它却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过程,以至于没有任何零售商敢于忽略它!
如果没有来自零售行业的强劲广告收入,Google云可能根本无法经营下去。2021年底,Google是全球第三大公有云基础设施(IaaS & PaaS)厂商,但只有9%的市场份额,远远落后于AWS和Microsoft Azure。由于Google既缺乏Amazon的先发优势,又缺乏Microsoft的技术及产品积累,它的公有云定位就很尴尬了:
AWS的优点是规模大、服务齐全、覆盖国家/地区众多,而且销售人员非常主动。对于零售行业的用户而言,使用AWS还可以与自身的Amazon渠道产生合力。
Azure的优点是继承了Microsoft的企业级产品,有助于实现无缝过渡。而且Microsoft以To B业务起家,非常理解企业的痛点,服务也比较到位。
Google Cloud既缺乏To B生态,也缺乏企业销售和服务意识。Google当然有一些“黑科技”,可是一般企业用户并不需要;Google也能提供Workspace等企业套件,但与微软的同类产品差了一个档次。
简而言之,如果你想做出一个“最主流的选择”,那可以大胆选择AWS;如果你高度依赖Microsoft生态,不妨选择Azure。在两头不沾的情况下,Google Cloud维持快速增长的杀手锏,竟然是价格战。尤其是2020年以来,通过激进的降价,Google Cloud的增速一度大幅超过AWS。从这个角度看,Google确实是在以赚钱的To C业务补贴亏钱的To B业务——Google Cloud到底能走多远,取决于Google还能从零售等广告主身上榨取多高的预算。
除了价格战之外,Google在To B业务上拥有的最大的王牌,无疑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方面的技术储备。早在2016年,Alpha Go作为第一个击败人类的围棋AI,就让世界认识到了Google的AI研发实力。根据Gartner的2021年度“魔力象限”(Magic Quardrant)报告,Google云平台的综合实力大幅度落后于Amazon和Microsoft, 仅能勉强维持“市场领袖”地位;但是,在AI开发人员心目中,Google云平台的地位极高,与Microsoft、IBM并列为第一集团,领先于Amazon。
显然,Google只有依靠AI技术,才有希望在公有云市场更进一步;而它的AI技术实力,恰恰来自于搜索引擎这个消费互联网场景,而且最早应用于搜索广告分发。整个2021年,Google最重要的技术应用,大概是“隐私沙盒”(Privacy Sandbox):该技术致力于在减少用户隐私收集的前提下,维持乃至提升广告推送的精度。Google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从而没有让广告收入受到合规要求的影响;Meta正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一点,才导致广告市场份额下降,市值也从最高点大幅缩水。我们将在下个章节详细讨论Meta的失败。
通过对Google (Alphabet)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意识到:To C业务可以成为To B业务最坚实的支点和资金来源、促使后者走向成熟,这是Amazon已经做到了的,也是Google梦寐以求的。哪怕我们做出最悲观的假设,即Google Cloud一直无法稳定盈利,而Alphabet的“其他尝试”也全部以失败告终,只要核心广告业务维持健康,Alphabet就可以有无穷无尽的资源,持续为未来下注。反过来说,假设Google广告业务出现明显的停滞或下滑,那么Google的其他一切业务都会减速,所谓Alpha-bet也将沦为笑柄。
任何人都不会否认Google在AI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但这种领先不是来自实验室的向壁虚构,而是来自搜索引擎带来的海量数据,并且首先应用于搜索结果和广告的优化。提高广告推送效率从而多赚几个铜板,看起来是一件很庸俗、很没有技术含量的事情;但是从击败人类的围棋应用,到今后登上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的太空船,都是源自这种“庸俗而现实”的需求。至于某些人想象的“一群科学怪人坐在高端仪表之间发明黑科技”的场景,仅仅是毫无现实依据的梦呓而已。
Meta: 在用户和商业化上的双重失败导致了掉队
截止2022年4月,Meta的市值仅相当于Alphabet的33%、亚马逊的37%;讽刺的是,即便在腾讯因为各种不利因素而大幅下跌之后,Meta的市值也仅为腾讯的1.35倍,与2020年底的差距大致相仿。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在“五巨头”当中,Meta是最有可能掉队的,这就是Mark Zuckerberg急于从“元宇宙”(Metaverse)寻找“第二增长曲线”的原因。
2021年,Meta大约98%的收入来自“Meta App家族”(Family of Apps),也就是Facebook和Instagram两款社交平台的广告收入。问题在于,Meta的广告收入表现不尽人意,最近一个季度的增速仅相当于Google广告收入增速的一半。至于“仿真实验室”(Reality Lab),即以Oculus为代表的VR硬件及软件业务,不但收入贡献极低,而且处于严重亏损状态。在Facebook全面拥抱“元宇宙概念”、改名Meta之后,市值曾短暂突破1万亿美元——此后就从这个最高点下跌了40%。投资者显然并不愿意为它的元宇宙愿景支付估值。
在中文互联网,有一种观点:Meta衰落的主要原因是TikTok的崛起,字节跳动将是Meta的“一生之敌”。这种观点有一些道理,但实在太简化、太不全面了。事实上,早在TikTok崛起之前,Meta在科技巨头中的掉队势头就很明显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Facebook这个核心应用的“老化”。最近几年,Facebook已经彻底沦为一个“中老年社交平台”,而且用户互动倾向很低,对广告主的吸引力每况愈下。与同属Meta旗下的Instagram相比,Facebook的用户年龄明显更大,具备时尚性和潮流性的内容占比也更低。
Meta管理层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试图通过发展Instagram的广告业务来弥补Facebook的衰落。这个努力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尤其是2016年推出的Ins Stories功能,成为了KOL承接广告的重要场所,产生了大量收入增量。从2021年开始,Instagram的广告收入可能已经超过Facebook,成为Meta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然而,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策略,不足以挽回Meta总体市场份额的下降。2021年四季度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
Meta广告收入同比仅增长19%,Google广告收入却增长了33%,Amazon来自第三方商家的广告收入也增长了32%。
Meta的广告收入仅相当于Google的54%;考虑到Meta的用户总数(按DAU或MAU计算)很可能高于Google,前者的广告变现效率实在堪忧。
来自TikTok的竞争压力当然也很大。2022年初,TikTok在北美的用户,有25%的年龄低于19岁,22%的年龄在20-29岁之间。也就是说,Instagram的用户明显比Facebook年轻,而TikTok的用户又明显比Instagram年轻。与其说TikTok是Meta的掘墓人,倒不如说它是Meta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后者早已因为产品和商业化方面的双重落后而摇摇欲坠,衰落几乎是必然的。
对于Meta而言,值得庆幸的好事有两件:首先,TikTok在印度被封禁,而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新兴市场,也是Meta App家族最重要的用户增长来源;如果印度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发展,Meta就可以将这个市场的用户优势转化为新增收入。其次,2021年TikTok在北美的用户增速已经放缓到25%左右,进入温和增长的轨道;Facebook + Instagram的用户即使在去重之后,对TikTok的优势仍然是明显的。然而,上述两件“好事”最多只能让Meta稳住防线,远远谈不上收复失地。
在2021年四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上,Meta管理层提出了2022年的七个“优先投资方向”:Reels(Instagram的短视频功能)、社群通信、电商、广告、用户隐私、AI和元宇宙。其中:
Reels取得了一定的用户参与度,但是Meta尚未披露具体的数据。即便按照最乐观的猜想,它也远远无法与TikTok相提并论,何况商业化几乎尚未开始。
社群通信主要是在Facebook Messenger和WhatsApp,最终目标是提供像Slack(以及国内的钉钉、企业微信)那样的企业通信服务;考虑到Meta的几乎没有企业服务的基因,对于这块业务实在无法乐观。
电商闭环一直是Meta的理想,但过去多年并无成就。Amazon+品牌官网/独立站仍然构成了美国电商市场的绝对主流。Meta希望通过直播及视频带货等形式杀出重围,可惜在这方面它很难压倒YouTube和TikTok。
广告是Meta的核心业务,管理层的想法是把它与电商结合起来,让商家更直接地触达用户、完成交易。显然,Meta需要先完成电商闭环,再通过电商去刺激广告收入——这个如意算盘不太可能成功。
AI扮演着各项业务的技术基础。Meta的AI技术水平显然难以与Google相提并论,很可能也比不上Amazon。由于收入和利润规模已经掉队,Meta很难在基础研发上投入足够资源,何况它还需要承担VR这个烧钱大户。
元宇宙被Mark Zuckerberg视为Meta的未来。问题在于,他选择的突破口是远程办公,这显然缺乏说服力。其他有志于元宇宙的公司,包括Epic Games、Roblox乃至国内的腾讯、米哈游,均是以娱乐内容(尤其是游戏)为主要突破口。Epic Games和Take-Two两大游戏公司的CEO都批评过Meta的元宇宙愿景,认为所谓在元宇宙内办公完全就是伪需求。此外,Meta的元宇宙研发几乎完全押注于以Oculus VR硬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系统。
最后,用户隐私是导致Meta收入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在iOS系统下,互联网广告平台高度依赖广告标识符(IDFA)进行广告效果的衡量和优化。所谓IDFA,就是iOS赋予每台设备的独一无二的可识别代号。例如,一个用户在Amazon搜索了某款手机的名称,被记录了IDFA,广告主就可以在Facebook向该用户定向投放手机广告;至于这个广告有没有促成用户的购买行为,也可以通过IDFA进行跟踪。iOS用户也可以自主选择关闭IDFA,但是在2020年以前,只有20%的用户这样做。
在2021年4月的iOS 14.5系统更新之后,任何App若想跟踪用户的IDFA,都要先弹窗取得用户认可。可想而知,绝大部分用户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根据Flurry Analytics的统计,在iOS 14.5更新发布之后,允许Facebook跟踪IDFA的用户,在美国仅有4%,在全世界仅有11%。当然,遭遇危机的不止Meta一家。IAB的调查显示,在iOS 14.5发布之后,有49%的广告主感觉在iOS设备上的CPM(广告千人成本价)有所提升。一般而言,越是发达的国家,iOS市场份额越高,广告行业受到的影响就越严重。
除了IDFA,Meta广告业务还受到了第三方Cookie收紧的影响。所谓Cookie, 就是网站为了辨别用户身份而储存在用户终端上的小型数据文件,一般用于浏览器端。广告平台或广告公司可以通过在大量网站中嵌入自己的Cookies, 来跟踪用户的跨域名(跨网站)浏览行为。例如,假设Facebook在数以百计的电商独立站中嵌入了Cookies, 就可以辨认出大量用户的购买习惯,从而对其精准推送广告。
随着用户隐私保护运动的深入,从2020年开始,主流浏览器开始默认禁用第三方Cookie;市场份额最大的Google Chrome, 则要等到2022年才会彻底禁用。可想而知,Meta在PC端和移动浏览器端的广告业务也将受到巨大的影响,虽然实际影响应该没有IDFA那么大。
投资者肯定会关心一个问题:Meta的广告业务固然受到了用户隐私保护政策的严重影响,但是为什么Google这样的竞争对手没有受到影响?Amazon的第三方广告业务好像也没有受到影响。对此,Meta管理层的回答是:
IDFA关闭主要影响的是iOS APP,而Google在iOS端的访问主要是来自浏览器,受到的影响较小。(然而,这无法解释为何Google不会受到Safari浏览器禁用第三方Cookie的影响!)
Apple与Google的关系比较好,因为Google网盟广告产生的收入会分给Apple,所以得到了区别对待。(缺乏说服力,因为Apple和Google的竞争关系显然要强于合作关系!)
资本市场怀疑,Meta广告业务受到冲击的罪魁祸首,是管理层无能、组织低效率和技术水平落后。自从2016年以来,欧盟和美国立法者就在寻求阻止科技巨头收集用户隐私,这几乎是一张明牌;iOS隐私政策的改变则早在2020年就提出了,到实际执行有大半年之久。遗憾的是,Meta未能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仅仅依靠抱怨和找借口,是坐不稳科技巨头的位子的。
鉴于Meta在收入和利润方面都已经被其他四巨头甩出很远,而且已经有了VR设备这个“大出血点”,它几乎不可能有剩余资源投向其他新兴业务。印度市场看上去很美,而且TikTok等中国竞争对手难以进入,但它无法提供Meta急需的收入增长。Meta商业化落后的趋势已经持续多年,这种趋势是源于Facebook平台丧失活力和影响力,而这一切的最终根源是战略和执行力的双重缺失。
Meta对于元宇宙的押注,与其说是高瞻远瞩的豪赌,倒不如说是“病急乱投医”。除非发生奇迹,或者管理层更迭,Meta无法在短期内摆脱困境。这就是Meta无论在市值上还是估值倍数上都远远逊色于其他四巨头的原因。
Apple:在绝对的资源优势下,一切“硬科技”都是纸老虎
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Apple缺乏研发能力,研发投入不足,仅仅是依靠工业设计和一体化生态系统取胜。从2021年四季度的财务数据看,这种说法有一定依据:Apple的研发费率仅为5.1%,而其他四巨头均在10%以上。然而,从研发费用的绝对值看,Apple甚至高于Microsoft, 与Meta相差不大。令人意外的是,在科技巨头当中,研发费率最高的是Meta(20.9%),而研发费用最高的是Amazon(153亿美元);反而是一般人心目中最擅长“硬科技”的Microsoft,无论按照哪个标准均处于较低水平。
事实上,研发费用和费率虽然对公司的技术实力有一定指导意义,但并不全面,横向对比的意义有限。原因很简单:
各家公司对“研发费用”的定义不同。例如,Amazon将技术研发和内容开发费用统一记录(Technology and Content),从而得出了一个虚高的数值。对于将什么样的人员和费用定义为“研发用途”,公司管理层一般有很大的裁量权,我们并不清楚其细节。
研发费用的一部分可能被资本化,从而降低当期数值。例如, Microsoft的软件产品在通过“可用性测试”之后的开发费用必须资本化,这很可能导致了其研发费用被低估。研发费用资本化往往是出于税务部门的规定,并非公司所能左右。
研发费率以营业收入为基数,受到收入确认政策的影响很大。像Apple这样的智能硬件公司,以及Amazon这样有自营电商业务的公司,收入基数本来就很大,由此导致了研发费率被低估。
即便不考虑会计因素,公司选择的研发方向也很重要:Meta的研发费用可能有30-50%花在了VR技术上,而该技术与公司主营业务关系不大;Alphabet的研发费用也有很多投向了与主营业务无关的“其他尝试”,其中绝大部分注定要失败。作为局外人,我们永远无法判断一家公司的研发费用有多少投到了“刀刃上”,不过苹果的研发费用显然产生了极佳的效果——我们将在后续部分详细论证这一点。
2021年第四季度(注:2022财年第一季度),苹果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11%,其中产品收入增长9%,服务收入增长24%;毛利润同比增长高达22%,其中产品和服务业务的毛利率均有提升。考虑到服务业务的毛利率明显更高,随着服务占比的提升,苹果的综合利润率仍有很高的上升空间,这也是资本市场看好苹果的根本原因之一。
我们认为,在收入规模已经很大(上一季度高达1239亿美元)的情况下,苹果正在从三个方面发掘下一阶段的增长点,可以称之为“三位一体”战略:
产品方面:iPhone产品线持续拓宽,实现从高端(Pro/Pro Max)到中低端(SE)的全覆盖。可穿戴设备和家用设备培养用户习惯,争取成为新的收入和利润担当。请注意,目前苹果的“可穿戴、家用设备和附件”业务中包括过时的iPod产品线;方兴未艾的iWatch和AirPods增速可能要高一大截。
服务方面:除了标配的iCloud以及App Store分成,大力发展Apple Music、Apple TV+、Podcasts等流媒体业务,构建Apple原生内容生态。截止2022年初,Apple Music的付费用户为9800万,而Apple TV+不少于2000万。与硬件业务相比,内容服务的毛利率明显较高,对Apple更有吸引力。
技术方面:在Mac、iPad等产品线中逐渐使用自研M系列芯片,在提升性能的同时,可能还会降低成本,由此进一步挖深Apple生态的护城河。按照中国投资者的标准,M1芯片已经足够让Apple跻身于所谓“硬科技”公司之列。
在历史上,Apple出品的Mac系列电脑经历过三次芯片转换。第一次是1990年代初,Apple与IBM、Motorola组成联盟,基于IBM的Power架构开发PowerPC芯片,并将其用于Mac。第二次是2005年,由于IBM无法解决PowerPC G5的功耗和散热问题,再加上Intel的产品路线图更有吸引力,Apple时任CEO乔布斯决定全面转向Intel设计和生产的x86架构芯片。后一次转型非常成功,见证了Mac性能的大幅提升和市场份额的复苏。但是,从2013年开始,媒体上频繁出现关于Apple不满于Intel芯片、计划以自研芯片取而代之的报道——2020年,谣传终于成真。
Apple转向自主研发芯片的原因有好几个。首先,Intel近年来的技术和产品进步缓慢,越来越不能满足Apple对性能提升的需求。其次,通过自主研发iPhone使用的A系列芯片,Apple已经积累了充足的芯片设计经验。再次,ARM架构日臻成熟,与x86-64架构在专业计算领域的差距日益缩小,让Apple有了以前者替代后者的底气。最后,作为全世界收入和市值规模最大的公司,Apple不但有足够的资源支撑芯片研发,也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由此产生的风险;即使尝试不成功,也不会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
十四年前,当Apple放弃PowerPC、转投x86时,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Mac不再坚持独特的技术路线,在硬件层面与一般PC的差异日益缩小,仅在软件层面维持差异。十四年后,Apple却带着自主设计的M系列芯片归来,而且成为了第一个全面转向ARM架构的主流电脑厂商。2021年发布的M1 Max,以及2022年发布的M1 Ultra,将Apple自研芯片的触角进一步伸到了高端个人电脑和工作站级。至此,Apple转向自研芯片的尝试以全面胜利告终,下一代芯片M2也在路上了。
除了性能优势之外,M系列芯片的市场策略也颇为老道:首先在MacBook Air、MacBook Pro两款笔记本以及Mac Mini便携台式机产品中推出;在取得市场认可之后,(在价格层面)向上延伸至iMac台式机、向下延伸至iPad Pro平板电脑;最后进一步向上延伸至Mac Studio工作站、向下延伸至iPad Air平板电脑,形成完整的产品线覆盖。尤其是在iPad Air当中使用性能强大的M1芯片,让其他所有平板电脑厂商处于尴尬境地,很难拿出像样的反击手段。
这种现象再次证明了强大的消费业务对“硬科技”研发的重要意义——Apple拥有销量庞大、覆盖各类用户层级的消费电子产品线,因此可以游刃有余地为自研芯片选择应用场景,稳步有序地实现芯片业务的扩张。在制造方面,Apple的重要性和体量使得台积电不得不予以认真对待,保质保量完成供货。可以想象,如果是一个独立厂商设计出了性能强大的PC级ARM架构芯片,在缺乏消费业务支撑的情况下,也很难在短期内将其推广开来。要知道,从2020年6月Apple官方宣布将换用M1系列芯片,到2022年3月整个Mac系列换装完成,只花了21个月而已。
截止2022年3月,Apple已经实现了在全部主力硬件产品中的芯片自研化:iPhone和HomePod使用A系列,Mac和iPad使用M系列,iWatch使用S系列和W系列,AirPods使用H系列。这种全面自研化不是出于计划,而是产品发展的自然结果。Apple构筑的生态系统足够强大,利润足够丰富,在产业链中的地位足够重要,从而具备了以合理的价格部署高性能自主设计芯片的能力。如果一个规模远小于Apple的硬件厂商要强行仿效,那么结局将是不言而喻的。
Apple的资金储备非常强劲:截止2021年底,现金及短期投资规模之和为639亿美元,而且其长期投资足以清偿一切债务;上个季度的经营现金流高达470亿美元。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Apple有能力以自主研发、投资或并购的方式,进军一切“硬科技”领域,只看它乐不乐意而已。在军事上,数量本身往往即意味着某种质量;
同理,在商业上,足够强大的财务资源往往即意味着技术实力,因为只要出价足够高,总归有人会乐意出售。对于这一点,Amazon可能更有心得,因为它的自研芯片、机器人和自动驾驶业务全是来自并购。而单纯寄希望于通过某种技术创新而实现单点突破的公司,成功的概率非常渺茫。就像一句成语:“欲速则不达。”
Microsoft vs. Amazon: 不同出发点的殊途同归
Microsoft是“五巨头”当中唯一一家以To B业务为大本营,而且迄今仍以To B为主要收入和利润来源的公司。Microsoft与其他“四巨头”在多种业务上有竞争关系,例如Surface平板电脑与Apple iPad及Mac竞争,Bing搜索引擎与Google搜索引擎竞争等等。
但是,与Microsoft竞争最直接、最激烈的巨头是Amazon。因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在于云计算,这既是Microsoft近年来得以复兴的基石,也是Amazon的重要现金牛和利润来源。在核心业务上形成的竞争,是最不可调和的竞争,何况双方的技术和规模差距不大。
有趣的是,观察Microsoft和Amazon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某种“异曲同工”或“镜像”:前者立足于To B,向To C扩张,近期收购Activision Blizzard更凸显了这个战略;后者立足于To C,向To B扩张,在Jeff Bezos卸任后的新一代CEO正是来自AWS。我们可否称之为“殊途同归”?虽然在上文已经对两家的发展轨迹进行了粗略探讨,但在本章我们将进行更细致的分析。
Microsoft:以To B为支点进军To C,反反复复二十余年
自从2014年Satya Nadella就任Microsoft CEO以来, Azure云计算业务取得了巨大进展,成为唯一能与AWS扳手腕的公有云服务。截止2021年底,Azure在全球IaaS & PaaS市场占据了22%的份额,仅次于AWS,并已经达到后者的2/3。Microsoft的云计算转型,远比Oracle、IBM等老一辈信息技术巨头更成功,因此市值也将它们甩下了一大截。
Microsoft Azure取得成功的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也是其他公司最难以仿效)的一点是在企业客户方面多年累积的优势。具体而言:
在PC时代,Microsoft软件产品深入影响了几乎所有主流企业客户,其影响力不仅体现在操作系统这样的“基础层”,也体现在办公、企业管理、应用开发、信息安全等“应用层”。选择Azure,就意味着将整个Microsoft软件生态比较平滑地迁移到云端。这对于那些历史悠久、不想重新部署软件解决方案的大中型公司尤其有吸引力。Microsoft成功地将企业客户对自身软件产品的依赖,转化为了对Azure云服务的依赖。
Microsoft的整个组织架构(包括但不限于销售部门)都是以服务企业客户为核心。尤其是在北美和欧洲,Microsoft非常熟悉企业想要什么、如何分配预算、如何做出IT采购决策。企业客户的决策往往比消费者更慢、更谨慎,更关心可靠性,对后续服务的要求更高;而且一旦做出决策,就带有很强的惯性。对于服务这种客户,Microsoft的经验和技巧要远远强于绝大多数消费互联网公司。
在Microsoft Azure的竞争对手当中,AWS虽然没有对企业客户的历史积累,但是其销售能力非常强大,而且先发优势过于明显,所以仍然维持着市场领先地位。而Google Cloud则既缺乏历史积累,也没有足够的对企业销售能力;Google内部流行的主要是21世纪诞生的消费互联网文化,也就是引领风气之先,在用户意识到需求之前就去创造需求——这恰恰不讨企业客户尤其是大客户喜欢。
云计算业务的强劲增长,使得Microsoft更有本钱发起对To C业务的进攻,主攻方向在于游戏,其中最令人注目的举动是2021年对ZeniMax的收购、2022年对Activision Blizzard的收购。自从1990年代后期涉足游戏内容业务以来,Microsoft对游戏业务的经营已经超过25年;从2000年发布初代Xbox主机、经营游戏平台业务开始,也经历了22年。
这个漫长的过程经历了很多失败,恐怕也只有Microsoft这样拥有近乎无限资源的公司能够支撑下来。总结下来,Microsoft的游戏扩张之路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1. 从1995年开始,Microsoft成立了游戏发行部门,并收购了一批游戏工作室,由此诞生了《微软模拟飞行》《帝国时代》等一批优质PC游戏。不过,当时游戏市场的主流在主机平台,而Microsoft尚未做好准备加入主机竞争,而是与日本游戏巨头Sega合作,为后者的Dreamcast (DC)主机提供软件和技术支持。遗憾的是,Sega在与Sony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Microsoft被迫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
2. 2000年,Microsoft发布了初代Xbox主机,与Sony、Nintendo两大日本主机厂商展开竞争。在Bill Gates的计划中,游戏主机承载了让Microsoft占领客厅、进入消费者日常生活的使命,战略意义很高。当时Microsoft的收入和市值如日中天,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投入硬件领域的竞争。此后几年,Xbox建立了强大的内容生态,给当时的行业领先者Sony PlayStation 2制造了一些麻烦。
3. 从2007年开始,全球金融危机促使Microsoft调整策略,时任CEO Steve Ballmer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视游戏。Xbox 360游戏主机因为成本过高而且出现严重技术故障,一度造成了巨额亏损。结果就是Microsoft的游戏业务出现了一定的收缩,许多自研工作室被出售或关闭,投资者甚至猜测Microsoft终将退出游戏业务。
4. 2014年Satya Nadella接任CEO之后,第一次重要收购的目标就是《我的世界》开发商Mojang——这意味着游戏业务再次成为一个发展重点。此后几年,Microsoft致力于打通Xbox主机和Windows PC平台,以“跨平台会员体系”吸引主流玩家;同时不断通过收购加强自研能力,直至2022年初发起震惊世界的、游戏行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收购。
事实上,在2021年完成对ZeniMax的收购之后,Microsoft的自研游戏阵容已经非常完善:在射击品类有《光环》《战争机器》《毁灭战士》《雷神之锤》《德军总部》,在角色扮演品类有《辐射》《上古卷轴》《废土》《天外世界》,在竞速品类有《极限竞速》,在即时战略品类有《帝国时代》《光环:战争》,在沙盒品类有《我的世界》。在收购Activision Blizzard之后,Microsoft将进一步稳固在射击、角色扮演两个流行品类的优势地位。
耐人寻味的是,在历史上,Microsoft几乎所有的优质自研游戏都是源于收购;为Xbox平台开发游戏的独立游戏开发商,很大一部分最终都被Microsoft收购了。这种“外延式扩张”当然会造成许多管理上的问题,通过收购获得的工作室很多又被拆分掉了,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
很多人大概会问:同样是进行性价比较低的外延式扩张,为什么Microsoft成功了,而国内的字节跳动和B站尚未取得成功?答案显而易见——因为前者投入的资源总量远远高于后两者,投入时间也远远长于后两者。无论是多么低效的扩张模式,只要投入足够了,总归会有成功的那一天。关键看你等不等得起。
应该承认,目前Microsoft的游戏战略,比以前更加清醒、务实。它意识到了,如果单独比拼游戏主机平台,Xbox很难打败Sony PlayStation;如果单独比拼游戏内容,它也不过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内容商,收入甚至小于腾讯;如果要比拼游戏主机之外的平台,那么在PC端已经有了强大的Steam,在移动端已经有了App Store和Google Play。上述任何一个领域单独拿出来,Microsoft都没有多少胜算。
因此,Microsoft的选择是:打通Xbox主机端和Windows PC端,然后进一步通过云游戏打通移动端,打造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跨平台”发行和渠道体系。当Sony和Nintendo仍然在以“独占游戏”为自家主机的卖点时,Microsoft早已放弃独占策略,转而鼓励跨平台内容,并将自己的游戏会员体系Xbox Game Pass扩展到PC端。
在历史上,Xbox Game Pass的规模一直逊色于Sony PlayStation Plus,后者的付费用户是前者的约2倍;但是,前者正在采取更激进的竞争策略,包括免费提供一些重量级首发游戏。在收购Activision Blizzard的电话会议上,Microsoft管理层公然提出,《使命召唤》这样的3A大作也可以在发售之日就向会员免费发放,这无异于对Sony的釜底抽薪。
Microsoft的最终目标是改造整个游戏行业的商业模式,实现所谓GaaS (Game as a Service)。在云游戏大面积推广之后,游戏主机、PC、移动平台的区别会无限缩小,买断制付费模式也将逐渐转向按时间支付会员费,就像今天Netflix等流媒体平台的商业模式。Microsoft对云游戏愿景十分乐观,因为它本身是全球第二大公有云服务商,数据中心遍布140个国家,所以在技术上和成本上都拥有优势;在此基础之上,只要补齐内容上的短板就可以了。严格地说,Microsoft的游戏战略最不可或缺的基石就是Azure!
相比之下,老对手Sony的应对方式要保守得多:没有对会员免费首发游戏的计划;云游戏服务仅覆盖PlayStation主机和PC,暂未延伸至移动端;会员使用云游戏服务的代价也要略高一些。与其说这是差异化竞争,倒不如说是一种无奈——Sony缺乏云计算技术优势,它的云游戏还要使用Azure的基础设施。它唯一的优势在于内容的数量和质量;可以想象,一旦这个优势也被追上,又会发生何等惨剧?当Microsoft收购Activision Blizzard的消息传出时,Sony花费27年建立起来的游戏生态,走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
如果没有云计算市场的领导地位,即便Microsoft愿意在游戏业务上继续投入,也不可能有很大的胜算。这是To B业务反哺To C业务的一个最佳案例。换一个角度,如果Xbox云游戏服务成为了市场主流,就将为Azure创造更多的内部及外部需求,从而帮助其进一步缩小与AWS的差距。现实就是如此奇妙,“为企业按需提供计算能力”与“占领消费者的客厅” ,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关的愿景,却产生了真实而深远的协同效应。
游戏并不是Microsoft唯一的消费业务。它还拥有LinkedIn(注:在财报中被列入企业业务而非个人业务)、搜索和新闻广告(主要是Bing)、硬件设备(主要是Surface)三个重要的消费业务板块。面向个人用户的软件产品和云服务也有较大的规模,但在本质上与面向小企业的此类业务没有本质区别。2021年第四季度,LinkedIn和广告业务增长比较强劲,主要是受到了后疫情时代美国经济复苏的推动。附带说一句,Microsoft广告业务的增速明显慢于Alphabet(尽管规模明显小于后者),Bing迄今也没有任何挑战Google的迹象。
可以看到,LinkedIn和Bing这两项消费互联网业务,处境比较尴尬:前者是垂直领域的领先者,可是横向扩张的空间有限,战略意义不明显;后者理论上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可是在Google这个过于强劲的对手的重压之下,毫无翻盘的希望。在长期,Microsoft只能寄希望于将它们与自身的To B业务结合起来,产生类似于“游戏+云计算”的协同效应——希望不是很大。反而是其中规模最小的Surface硬件业务,蕴含着一定的战略潜力。
Surface是Microsoft第一个真正实现了商业成功的智能硬件产品线。很多用户至今还记得Zune音乐播放器,它曾经被寄予与iPod竞争的厚望,最终却沦为笑柄;以及搭载了Windows Phone操作系统的Lumia手机,Microsoft不惜收购了Nokia的手机业务,最后却连整个Windows Phone生态都被放弃。所以,当初代Surface于2012年发布时,就算是最乐观的人,大概也不敢预测它能够持续十年以上,并且从2015年开始实现盈利。
我们很难衡量Surface究竟有多成功,因为市场调研机构往往会把它的不同型号拆分到“平板电脑”(Tablet)、“笔记本电脑”(Laptop)乃至“桌上电脑”(Table PC)等多个领域,从而低估其市场份额。如果我们粗略地把Surface归类为“平板电脑”,那么2021年第四季度,它的销售额大致相当于Apple iPad的30%,全球市场份额居于第三或第四位——第二位是Samsung;如果Google Chromebook算一种平板电脑,它的市场占有率可能也高于Surface。
仅仅从收入、利润或市场份额看,Surface似乎不是很重要。不过,从战略视角看,这条智能硬件产品线至少具备两个不可替代的意义:
自从Lumia手机偃旗息鼓、Windows 10 Mobile被放弃以来,Surface就成为了唯一的搭载Windows系统的移动智能设备。正是因为Surface的成功,HP、Samsung、Dell等厂商才推出了自己的类似设备,由此产生了“桌上电脑”这一品类。假设没有Surface, Windows系统可能会把教育、家庭等场景拱手让给Apple MacOS/iOS。
Microsoft可以通过Surface探索硬件开发的更多可能性,从而仿效和追赶Apple。例如,Surface Pro X使用了Microsoft和Qualcomm联合开发的Microsoft SQ1系统级芯片;由此发展下去,Microsoft像Apple那样推出自主设计芯片也不是不可能。毕竟,拥有自己的消费硬件产品,就意味着给很多基础研发成果找到了试炼场。
Zune,Lumia,Surface: Microsoft消费硬件进化论
为什么Surface能成功,而Lumia手机却失败了?一个重要原因是,前者搭载了台式机使用的Windows 8/10/11操作系统,从而具备了强大的“生产力”;后者搭载的却是Windows Phone 7/8,一个悲惨的“四不像”。让很多用户选择Surface的主要因素就是它能运行Office等生产力工具,而且与PC端实现无缝互动。对于那些希望让平板电脑同时承担娱乐和工作职能的人而言,Surface可以在办公室之外的场景发挥重要作用(经常随时随地加班的中国用户可能对此深有体会);在这种场景下,Microsoft生态系统可以拥有与Apple生态系统同样不可或缺的用户黏性。
只要理解了上面的一切,我们就能理解为何Microsoft决定从2020年起彻底放弃Windows Phone生态,仅保留搭载Windows 10/11系统的Surface产品线。无论是Apple iPad/Mac设备还是Android设备,在便携性、娱乐性和工业设计方面都达到了极高水平,而Windows生态与其竞争的最大优势在于生产力。Surface找准了自己的定位——生产力与娱乐兼顾的最佳组合,或具备一定娱乐功能的入门级生产力设备。这是Microsoft所擅长的战场,尽管它尚未取得全胜,但前途至少是值得期待的。
Microsoft在根本上仍是一家“To B基因”公司,无法与那些武装到牙齿的“To C基因”公司进行平等竞争。然而,每个人都有两面——既是办公室里的模范员工,也是躺在床上看电影的吃瓜群众;既是课堂里勤记笔记的学生,也是给朋友分享热门社交媒体的派对动物。这两面的需求不一定要由同一家公司满足,很多人早已习惯了工作时间归Windows生态、休闲时间归iOS生态;但是,总归有人希望以一部设备满足两种需求,而这正是Microsoft的希望所在。
需要补充的是,Microsoft在To C业务上暴露出了这么多缺点,恰恰是因为它是唯一一个有资格角逐To C巨头地位的To B公司。在1990-2000年代与它互有胜负的那些传统软件巨头,在业务和财务上都被甩出了很远的距离,可能永远不会获得同样的挑战资格。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若IBM、Oracle等公司得到进军消费市场的机会,其表现会比Microsoft更好。
Amazon: To B和To C均在进攻,但是态势不同
作为Amazon的利润担当和“现金牛”,AWS面临着Microsoft Azure的挑战。Google Cloud的增速固然很高,不过规模尚小;Azure才是真正的心腹之患。让Amazon股东高兴的是,从2021年二季度开始,AWS的增速持续回升;根据管理层的解释,这一方面是由于企业客户的需求在后疫情时代集中爆发,一方面也是由于销售团队的扩大。
迄今为止,AWS仍是全球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善的公有云服务,而且仍然是大批技术标准的实际制订者。只要它能将自身与Azure的收入增速差距控制在10个百分点以内,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上文提到个,考虑到AWS的营业利润率高达30%,它完全可以以激进的价格战打击竞争对手;既然它还没有这么做,就说明问题还不是很严重。
在2021年四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上,Amazon管理层表示,今后一年的资本开支(Capex)的主要用途如下:40%投资于IT基础设施,主要是AWS;30%投资于仓储设施;25%投资于配送能力;5%投资于其他领域。看起来,AWS仍然是重中之重,但还有两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对仓储和配送的投资比例之和为55%,说明Amazon最看重的仍然是物流履约能力。在2020年上半年的疫情初期,Amazon配送时间一度大幅延长,这刺激了它进一步建设物流基础设施。疫情期间,独立站、D2C品牌对欧美消费者的吸引力大大提升,如果Amazon想维持竞争优势,就必须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尤其是在生鲜、日用食杂领域。
对AWS的投资,有一部分会用在流媒体等娱乐业务上。Amazon内部业务本来就是AWS最大的客户,只是不会体现在财务报表上;随着Amazon Prime Video、Amazon Music、Twitch等娱乐业务的发展,内部业务对AWS的贡献比例可能有增无减。
对于Amazon在生鲜和本地电商方面的扩张,我们将在后续章节详细分析。Amazon管理层在这个领域投入的精力,很可能超过了AWS——因为后者是一个成熟的强势业务,前者则是一个发展初期、谁也不知道路径的业务。接下来我们主要分析Amazon的娱乐业务,它的重要性无法体现在财务报表中,所以经常被投资者忽视。
根据ComScore的统计,截止2022年初,Amazon Video可以触达63%的美国OTT(电视机顶盒)用户,仅次于Netflix和YouTube,遥遥领先于其他长视频平台;Amazon占据了美国OTT用户观看时长的9%,仅次于Netflix(26%)、YouTube(24%)和Hulu(13%)。其中,YouTube主要是一个PUGC平台,长视频占比较低,付费会员还在发展中;Amazon的主要竞争对手,其实只有Netflix和Hulu而已。
进入2022年,Amazon Video在内容领域的进攻态势有增无减,其中包括与美国NFL签订的为期11年的《星期四晚间橄榄球》(Thursday Night Football)独家播出协议,即将于9月开播的《指环王》系列剧集,以及多部由Amazon独家播出的大电影。现在,Amazon Video几乎就是一个缩小版的Netflix,能够与后者提供相似数量、相似品类的内容,只是内容质量和影响力尚远远低于后者。
肯定会有人好奇:在Netflix强大的先发优势以及对内容的深刻理解面前,Amazon究竟有什么竞争力?后者固然可以砸钱,但前者也不缺钱,而且砸钱做内容的商业模式就是由Netflix引领出来的。答案在于捆绑销售和价格优势。在美国等大部分国家,购买Amazon Prime会员(14.99美元)即自动获得Video会员资格;如果单独购买Video会员,则仅需要5.99美元。而Netflix的三个档次会员价格分别为9.99美元、15.49美元和19.99美元,用户成本明显更高一些。
你或许会认为,鉴于Netflix的内容优势明显,这样一点价格差异算不了什么。问题在于,对于已经购买了Amazon Prime会员的人而言,Amazon Prime Video相当于是白送的,Netflix被迫进入了一场不平等的竞争。2021年四季度,Amazon Prime有2亿会员观看过视频,而Netflix的全球会员也不过2.21亿。作为一个行业的领先者,在用户基数上被第二名追到这么近的距离,已经足够产生危机感了。
事实上,如果单纯比较内容库的大小,Amazon更胜一筹,合计拥有2.6万部电影和2700部剧集的版权(2021年底数据),而Netflix仅能提供3600部电影和1800部剧集。所谓“Netflix的内容优势”,主要是指新内容,尤其是每个季度的独家剧集。最近几年,Netflix甚至在主动收缩内容数量,淘汰旧内容、聚焦于新内容。一般而言,资深影迷会更喜欢Amazon涵盖一切的内容库,而普通用户会更渴望在Netflix上看到一线剧集。从这个角度看,Netflix并不能做到Amazon所能做到的一切,它的内容优势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大。
在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Netflix还可以稳坐钓鱼台,因为那里的用户早已养成观看习惯,而且对价格不太敏感。然而,在印度、拉美等新兴市场国家,Amazon的捆绑销售可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要知道,Amazon Prime会员除了绑定视频, 还绑定了音乐、游戏、电子阅读、直播频道等一堆数字内容服务,这对于尚未形成使用习惯、预算又有限的用户可能很有吸引力。恰好近年来Netflix的发展重点也是海外新兴市场,可以想象,它与Amazon在用户方面的竞争将会日趋激烈。
外界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Amazon对媒体及内容业务的扩张早在1998年就开始了,当时它的第一次重大收购目标就是IMDb电影资料库。因为早期的Amazon是一家网上书店,书籍本身就带有内容属性;此后多年,它也从未放弃过对内容业务的野心:
2006-2010年,先后成立或收购了视频、在线音乐、电子阅读、有声书、实体书和影视制作业务,从而具备了比较完整的内容产业链。然而,这个时期Amazon的财力还不是很强,尚未坐稳“科技巨头”的位子,大部分资源被用于电商和云计算两大业务;上述媒体业务的发展普遍比较缓慢,在细分市场处于边缘地位(电子书除外)。
2012-2014年,随着AWS开始贡献利润,Amazon有了更雄厚的本钱。它一方面加码视频平台和影视业务,一方面开始从事游戏这个最烧钱的内容业务;对Twitch直播平台的收购,同时支撑着Amazon对游戏和流媒体业务的野心。在这个阶段,Amazon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拥有内容业务”,而是致力于把内容业务做成下一个增长点。
2019年,Amazon开启了IMDb TV,目标是与YouTube竞争。2022年,它收购了好莱坞传统“六大”公司之一的MGM。在巨额投入之下,视频业务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游戏业务虽然规模还不大,但也有几部成功作品问世。在Amazon季度财报当中,娱乐板块被置于“管理层讨论和分析”的第二位,仅次于电商板块,可见管理层的重视程度。
Amazon扩张内容业务,显然不是为了与Amazon Prime会员形成交叉销售,因为这个会员单纯依靠免费送货服务就可以卖得很好了。我们应该从更高的层面思考这个问题。首先,就像Microsoft通过云游戏与自身的Azure云服务产生协同性一样,Amazon也可以通过流媒体平台与自身的AWS产生协同性。
其实,从AWS成立之日开始,Amazon内部业务就是它最大的单一客户(只是不会显示在财报上);Amazon电商平台的对存储和算力的庞大需求,推动了AWS的快速增长,从而使其能为外部客户提供更全面、更廉价的服务。现在,Amazon Prime Video可以继续扮演这种内部驱动力的角色。附带说一句,Netflix使用的也是AWS云服务(正如Sony云游戏使用的是Azure云服务)!
其次,在所有消费互联网业务当中,零售电商业务是打开频次较低、用户基数较小的一种。Amazon不在财报中公布用户数量,但我们估计其电商平台的DAU/MAU远远低于Google和Meta,正如国内淘系电商的DAU/MAU远低于微信和抖音。美国互联网公司不像中国同行那么重视用户数量和用户时长概念,可也并非毫不重视。如果能够以可控的成本经营媒体和内容业务,从而提升Amazon生态系统的用户基数和用户黏性,无疑是值得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Amazon在To B和To C两个方向均在进行扩张,但是形势的复杂程度完全不同。在To B领域,AWS的领先优势仍然明显,主要是沿着既定轨道加大投资,在更多国家推出更多服务种类,同时增强在SaaS层的存在;这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主要比拼的是执行力。
在To C领域,Amazon主攻的则是近场电商(生鲜、日用食杂)和内容业务,前者是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后者则不是它在历史上擅长的业务。关于近场电商的问题,后面将有专章讨论;内容业务则需要与AWS互为支点、互相助推。在这里,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对于Microsoft和Amazon这种级别的科技巨头而言,既没有单纯意义的To C业务,也没有单纯意义的To B业务,一切都是互相关联的。
From To B or To C? “跨境扩张”的难点所在
Microsoft以To B业务为出发点进攻To C,Amazon以To C业务为出发点进攻To B,二者迄今均已取得了不错的成效。那么,谁的效率更高、表现更好呢?公允地说,是Amazon。我们只需要注意到如下事实,即可得出上述结论:
Microsoft早在1995年就开始经营游戏业务,早在2006年就开始经营智能硬件业务。经过多年探索,它在这两个方面只能算“站稳了脚跟”,还远远谈不上“市场领导者”。在此期间,Microsoft犯下了太多错误,付出了沉重代价,完全是依靠在软件行业积累的雄厚资本,才支撑着To C业务没有倒下。换了其他任何一家公司,恐怕都无法付出类似的代价,过去的一切投入终将沦为笑柄。
Amazon从2004年开始经营公有云业务,几乎一手创造了现代云计算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短短十年之内,AWS不但实现自给自足,而且开始反哺自营电商业务。作为一家新兴公司,Amazon没有很高的容错率,基本依靠效率和创新精神打赢了这一局。AWS在云计算行业的地位,要远远高于Xbox在游戏行业的地位、Surface在平板电脑行业的地位,这一点应该毫无争议。
消费者和企业客户存在太多区别:前者比较感性、决策周期较短、用户体验要求极高,后者比较理性、决策周期较长、不太重视用户体验;面向两者的销售体系并不通用,一个品牌的号召力往往不能无缝地同时覆盖两者。换句话说,一只“大笨象”可以做好企业生意,甚至会被企业客户认为稳重可靠;在消费者那边,“大笨象”却几乎毫无可取之处。
2000年,Microsoft发布的初代Xbox游戏主机,就是这样一只“大笨象”:缺乏工业设计,傻大黑粗,塞满了笨重的标准化硬盘和DVD光驱,就连名字也有点拗口。这样一台设备,非常不适合放在客厅或起居室里,连搬运都很吃力,仅此一条就注定要失败。彼时彼刻,Apple正在通过工业设计推出一个又一个爆款消费级产品,Microsoft却没有从中学到任何东西;此后十年双方的消长,在此刻其实已经决定了一半。
笨重的初代Xbox主机,塞下了太多部件
你或许会反驳:“Xbox不但没有失败,反而取得了2400万部的销量,为Microsoft的游戏平台事业开了一个好头!”没错,那是用无休止的砸钱换来的——Xbox的定价远低于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了极高的性价比;在主机上市前,Microsoft火速收购了一批游戏工作室,又重金买下了一批游戏的独占权;铺天盖地的广告和营销攻势也震动了整个游戏行业。
到了下一代Xbox 360主机发布时,Microsoft不仅再次因为成本过高而蒙受巨额亏损,还因为品控不力而酿成了“死亡三红”恶性故障。幸亏竞争对手Sony也犯下了类似错误,Microsoft的损失才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否则Xbox系列主机可能早已二代而终。
在其他消费级业务中,Microsoft不停地重复着恶性循环:由于产品设计不佳,导致用户体验不好,只得砸钱(降价或收买合作伙伴)解决问题,同样的问题又会在下一代产品中出现。直到实在无钱可砸,或者管理层不再愿意付钱,该业务遂关门大吉或无限期停滞。这样的命运,曾经出现在Zune音乐播放器、Lumia手机、Kinect体感设备、HoloLens VR设备身上,还曾差点出现在整个Microsoft游戏业务身上。
在企业级业务上的大量积累,本来应该使Microsoft获得一定的技术优势,以构成对消费端的“降维打击”——这是很多投资者一直盼望的。遗憾的是,企业级业务往往会使Microsoft背上历史包袱,用做企业产品的思路去做消费产品生态,由此导致了Windows Phone的悲剧,以及Microsoft彻底退出智能手机市场。
2010年,智能手机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Android羽翼未丰,Nokia等传统厂商未能及时推出自己的软件生态;而Microsoft拥有Windows CE、Windows Mobile等早期移动操作系统的积累,在理论上具备以Windows生态实现PC端和移动端“大一统”的可能性。然而,Windows Phone操作系统的短暂历史,就是一部合作伙伴的血泪史:WP7抛弃了以前版本的一切应用生态,第三方开发商必须从头开始;WP8则不支持大部分旧设备的升级,从而惹怒了第三方硬件商和最支持WP的老用户。到了2015年,WP系统又被全面改版为Windows Mobile 10,整个应用生态再次重启;不过反正也没什么区别了,因为Microsoft已经彻底输掉了智能手机市场的竞争。
有趣的是,自从2014年Satya Nadella接任CEO以来,Microsoft的各项消费业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复苏。这是否说明新的管理层更擅长消费业务,或者对企业文化进行了面向消费者的改造?不一定。还有两个更合理的解释:第一,Microsoft交了这么久的学费,总归交到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开始懂得服务消费者了;第二,云计算为Microsoft创造了巨大的利润和现金流、提升了团队士气,使得消费业务获得了更多资源和更宽松的条件。如果在未来3-5年内,Microsoft的各项消费业务能继续取得不错的战绩,我们才能说它的“从To B到To C”的扩张取得了全面胜利。
反过来说,为何Amazon从To C到To B的扩张,成效明显更快、代价也较小呢?运气因素是很重要的,这种成功可能不具备广泛的指导意义——Google和Meta对To B业务的扩张就远远没有那么高效。然而,Amazon的成功仍然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其中的核心驱动力可以称为“消费互联网公司的天然活力”。
消费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边际成本最低、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最高的一门生意。因此,消费互联网公司必须是“快公司”,极端重视产品迭代和客户服务的效率,才能在九死一生的竞争中存活。必须指出,企业级业务不一定需要“快公司”,很多企业客户重视稳定远胜于重视效率。但是,在云计算这个全新的领域里,快速反应就意味着制订技术标准、掌握话语权、塑造客户使用习惯。
从2003年夏AWS负责人Andy Jassy提出云计算的初步理念,到2005年AWS基础云服务小范围测试,只过了不到两年;又过了三年,AWS的“数据库、存储、分布式计算”三位一体的能力已经完全成型。我们很难想象,在消费互联网行业之外的任何一家公司,能够在这么重要的业务上达到这么高的效率。
严格地说,Google在云计算业务上的扩张效率也不低:2008年宣布,2010年开始提供存储服务,2012-13年开始提供计算服务,2016年以后即稳居全球公有云IaaS & PaaS市场的前三名。相比之下,IBM从2013年才通过收购进军云服务,Oracle则直至2016年才开始提供公有云服务;缓慢的反应速度,使得这两家传统软件巨头永久失去了在云计算市场领先的机会。在中国的情况也差不多,阿里巴巴是最早拥抱云计算趋势的公司,其次是腾讯;在传统信息科技公司当中,只有华为及时做出了反应。
换一个角度思考,消费互联网公司之所以具备更高效率,除了行业本身的特性使然,或许还有企业发展阶段的原因——想当年,Microsoft、Oracle创立之初,都曾经以“快公司”而闻名!在任何企业的初创期,组织结构总是比较扁平,管理层总是有危机意识,部门内耗也还不太严重。随着组织规模扩大,官僚主义不可避免地产生,管理层和早期员工也逐渐开始自满、出现路径依赖。二十年后的互联网行业会不会像今天的传统软件行业那样低效率?或许用不了二十年?
AWS宣称,它能取得成功是因为能更好地服务客户,归根结底是因为它具备Jeff Bezos所谓的“第一天思维”:专注于客户,避免官僚主义,勇于孵化新能力,接受而不害怕失败,组织结构灵活,以有创造力的小团队为基础,优先考虑长期价值而非短期价值,等等。上述“第一天思维”是Amazon特有的吗?显然不是。任何创业公司在取得初步成功的阶段,大概都具备“第一天思维”;随着组织结构的膨胀,又不可避免地转向“第二天思维”。其实,很多Amazon内部员工也在抱怨官僚主义和组织运转不灵,今后类似的抱怨可能会越来越多。
在国内,很多投资人曾经拼命鼓吹字节跳动、拼多多、快手等“新一代公司”具备高超的执行力或组织效率,远远强于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上一代巨头”;经过2021年的残酷风浪,上述神话已经破灭了一半。即便神话是真的,一家仅有10年历史的公司的组织效率高于有25年历史的公司,也不是什么难以解释的事情,前者终归也会遇到后者的一切麻烦。
Jeff Bezos所标榜的“亚马逊第一天思维”
话说回来,我们也不能完全用“发展阶段不同”去解释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别。在五大科技巨头当中,Apple和Microsoft成立于1970年代,Amazon和Alphabet成立于1990年代,Meta成立于2000年代;可是我们完全看不出Meta的组织效率高于Amazon或Apple。一言以蔽之,成立时间长短只是影响企业效率的诸多变量之一。消费互联网是近二十年来发展最快、变数最多的行业,这个行业的公司当然会获得一定的“效率加成”。至于下一个获得“效率加成”的行业会是哪一个,那就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了。
有必要强调一点:效率或反应速度从来不是决定商业竞争成败的唯一原因。无论在消费级还是企业级市场,客户有时候喜欢产品快速迭代,并愿意接受新产品的瑕疵;有时候则喜欢“慢一些但稳一些”的产品,甚至为此付出溢价。
不过,在大部分情况下,“快公司”要把速度降下来是比较容易的,“慢公司”要把速度提升上去则比较困难。或许这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从To C业务向To B业务的扩张,要比反向的扩张稍微容易一些。
Alphabet vs. IBM:硬科技的核心问题在于应用场景
IBM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一家信息科技公司。它不但主宰了计算机行业在PC出现之前的历史,而且亲手创造了PC产业。虽然在1980年代一度陷入危机,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IBM在Louis Gerstner的领导之下成功回到了一线巨头的位置(尽管仍然远远落后于Microsoft这样的新一代公司)。IBM对人工智能的投资可以上溯到1990年代,很多人至今还记得“深蓝”超级电脑在国际象棋中击败人类的报道。2010年代,IBM又推出了Watson这个“基于自然语义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试图以此为支点彻底改造人类的商务和政务活动。
然而,2022年4月的IBM,市值仅有约1100亿美元,远远低于上文提到的“五大科技巨头”。IBM Watson早已沦为历史遗迹,现在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是Alphabet (Google)开发的Alpha Go在围棋中击败人类的一幕;Alphabet与Amazon、Microsoft一道,成为了新的人工智能三巨头(有人认为Meta是第四巨头)。无论人工智能在今后二十年能发展到什么阶段,IBM的受益程度将注定小于Alphabet这个后辈。
IBM和Alphabet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此消彼长,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前者没有找到最合适、性价比最高的应用场景,而后者找到了。因此,Alphabet是在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前景,基础研发和应用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而IBM的惊世豪赌则以惨败告终。“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则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IBM:一部追逐“硬科技”应用失败的总记录
在中国资本市场趋之若鹜的“硬科技”领域,IBM一直不缺乏成果。毫不夸张地说,越是前沿、越是不接地气的研究方向,IBM的存在感往往就越强;如果一项研究项目还停留在实验室里,那它很可能就是IBM精通的项目。
当下最典型的例子是量子计算(Quantum Computing),被学术界视为传统(电子)计算机的潜在颠覆者,但是离大规模实用还非常遥远。IBM Q System One不但是世界上第一部基于线路(Circuit)的量子计算机,而且是第一台投入商业运营的量子计算机。虽然实际商业价值非常有限,这个成就仍然得到了无数媒体的报道,并且必将在IBM印发的各种PPT当中反复被强调。
IBM Q System One, 世界上第一台量子线路计算机
熟悉历史的人不妨大胆预测:一旦量子计算开始大规模投入实用,IBM的领先地位即使不丧失,也会大打折扣。这家老牌科技公司有能力维持基础研发投入,却总是在寻找应用场景上落后于那些更新潮、更灵活的公司——以前是Microsoft, 现在是Alphabet。我们不需要寻找遥远的例子,只需要回顾IBM Watson这个高开低走的大型泡沫就足够了。
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且从1990年代开始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这份研究报告中,我们没有必要讨论二者的微妙区别,只需要了解机器学习更重视大数据、强调通过海量数据的训练去自动提高算法精度即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算法可以代替人类解决越来越多的智力问题,就像机器已经代替人类解决了大部分体力问题一样。有人将机器学习视为下一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并非没有道理。
IBM不可能缺席如此重要的前沿技术。早在2016年,它就启动了Watson项目,目标是在自然语义下实现复杂的人机问答。也就是说,用户可以以日常语言向计算机提问,无需将其转换为代码,即可获得专业的、可理解的回答。2011年1-2月,IBM Watson取得了一个万众瞩目的开局:在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电视智力竞赛节目“Jeopardy!”当中击败了两位人类冠军,并获得了100万美元的大奖。同年,IBM宣布Watson已经达到了医学院二年级学生的知识水平。
雄心勃勃的IBM决定利用Watson改造整个西方世界最复杂、资源浪费最大的行业——医疗,而且一上来就聚焦于难度最高的癌症诊疗。2013年,包括德克萨斯大学MD Anderson癌症中心在内的三家大型医疗机构与Watson签约合作;IBM市值的历史最高点,也恰好出现在这一年(比现在高25%)。2015年,Watson Health正式成为了IBM旗下的一个独立部门。与此同时,Watson在教育、交通、工程、政务、天气预报等领域也得到了一定的应用。人们有理由相信,IBM将成为机器学习产业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然而,IBM Watson此后的历史,给“技术泡沫”这个词做出了最佳注脚。从2018年开始,每年都有大批医疗机构与Watson解约;2019年,IEEE Spectrum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论述Watson为何不能完成自己的承诺;2021年,IBM终于决定出售Watson Health的大部分资产,由于买家兴趣平平,直到2022年才出售完成。综合看来,Watson的失败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对癌症治疗的建议效果不佳。具体而言,Watson的治疗建议与人类专家建议的一致性较低,导致许多医院拒绝予以采信。当然,人类专家的建议未必就是对的,可是在癌症治疗这种大事上,没有人敢轻易用人工智能否定人类专家。此外,Watson的适用场景有限,只对肺癌等常见癌症有比较高的精度。
无法融入已有的医疗信息和数据系统。在MD Anderson癌症中心,Watson甚至无法接入电子病历系统;在英国,Watson也经常无法读取实际病历。原因一方面在于监管(病人隐私保护),另一方面在于医疗系统的复杂性。让Watson接入所有医院的医疗信息系统(HIS)简直是难于登天!
无法直接代替医生的劳动。Watson Health的设计初衷是减轻医生的工作负担,但由于技术和伦理的双重原因,它无法代替医生发表诊断意见,只能为医生提供参考。结果,在许多医院,Watson沦为昂贵的“年轻医生培训系统”,资深医生的工作量并未得到很大缓解。
说到底,IBM选择医疗作为突破口,本来就错了,因为医疗涉及到太多既得利益,又有太多伦理问题;选择癌症诊疗作为细分市场突破口,更是大错特错,因为医疗机构对于癌症这种重症的治疗手段必然是非常保守的,很难相信人工智能;选择以自然语义提供癌症诊疗建议,更是人为增加难度,妄想一步登天。事实上,直到2020年,医疗机构仍然在抱怨Watson对日常语言的理解能力不足。
IBM对Watson从希望到绝望的全过程,形象地体现在其年报中:2012年仅提及8次Watson,此后逐年剧增至2016年的131次,然后又一路回落至2021年的6次。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Watson有过回光返照的势头,可那是由于疫情期间个人用户大量使用Watson语音助手所致,与“高大上”的医疗服务没有关系。
假如IBM没有选择医疗这个极难改造的行业作为突破口,而是从一开始就聚焦于教育、交通等相对容易改造的行业,或许Watson的命运会大不相同。换一个角度想,IBM可不可以把Watson做成纯粹的消费应用,例如智能家居产品或智能机器人?毕竟,“自然语义识别”对消费者有很强的吸引力,即使是Siri和Alexa这种半吊子智能语音助手都能赢得用户青睐,何况是水平更高的Watson?可惜,历史不容假设。好高骛远、一味追求改变人类历史的结果,就是成为人类历史的笑料。
可惜的是,自从2005年出售PC业务以来,IBM基本失去了消费级业务,也就失去了对消费市场的感知。可以看到,IBM几乎从来没有认真地在零售、家电等消费行业推广Watson。2017年,IBM收购了一家广告代理公司,企图利用Watson指导广告投放——可是与Google、Meta高度成熟的精准投放技术相比,IBM又能有什么优势?就算IBM想把Watson技术带进千家万户,也要首先找到一个To C科技巨头作为合作伙伴。可想而知,Apple、Amazon、Microsoft应该都不会对此十分感冒。
由此可见,Microsoft在2007-3014年的困难时期,坚持不放弃消费级业务,反而一次又一次对智能硬件市场放弃冲击,又是何等高瞻远瞩。那是进入21世纪以来Microsoft与IBM市值差距最小的时期,也是两家走上根本性道路分歧的时期。附带说一句,IBM可能是历史上的所有信息科技巨头当中,唯一一家从未认真考虑开展任何消费互联网业务的公司。
当IBM在Watson押下重注之时,Google(后来更名Alphabet)的广告业务正处于黄金时期,而且这个黄金时期至今尚未结束。2011年,即Watson首次公之于众的那一年,IBM的营业收入是Google的2.82倍,净利润则是后者的1.63倍;到了2021年,即IBM拼命寻求出售Watson Health的那一年,它的营业收入仅相当于Alphabet的27%,净利润则仅为后者的6%。
2022年1月,IBM由于以约10亿美元将Watson Health的大部分资产出售,一个时代划上了句号;它同时宣布将改变战略,从此聚焦于“混合云和AI策略平台”。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了,因为IBM的财力已经不足以支持如此巨大的野心。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Alphabet即便在基础研发方面的实力,至少也不逊色于IBM。假设前者希望重复IBM Watson在医疗行业的冒险,虽然不一定能成功,但成功的希望很可能稍大一些——至少它可以多撑上一段时间。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提到:“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便构成基础。”对于企业而言,基础研发是比较高级的工作,必须以前台业务部门提供现金流、应用场景和生态系统支撑。这个道理本来是非常直观、不言自明的,遗憾的是,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真正理解的人似乎不多。
Alphabet:最远大的理想,以及最接地气的生意
Alphabet既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告平台(没有之一),又是全世界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成就最大的公司之一。上述两方面可谓浑然天成,因为广告本来就是机器学习最早、最重要的应用场景之一。Alpha Go在围棋这样复杂的智力运动中击败人类,当然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问题在于Alphabet不是依靠下围棋赚钱,也不是依靠比围棋更复杂的天气预测或癌症治疗赚钱;它赚钱主要是依靠在搜索引擎、地图等场景中搭载广告,赚钱效率则依赖于广告推送的精度。
2014年,麻省理工学院(MIT)就论证过机器学习对于广告行业的重要意义:与人类专家根据历史经验做出的判断相比,机器学习的判断能够将广告转化率提升12倍,而且通过机器学习获得的客户黏性(体现为续约率)要高出近2倍。从那时起,效果广告在互联网广告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自动化投放比例也越来越高。这个趋势的受益者不仅包括Alphabet、Meta和Amazon,也包括国内的字节跳动、阿里巴巴和腾讯。
与癌症治疗这种“地狱级难度”的应用场景相比,互联网广告投放堪称“简单难度”:在这个场景里,监管和伦理问题要少得多,做出成效要容易得多,也不存在大量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作为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地图和网盟服务商,Alphabet自己掌握着终端消费者,也就掌握了机器学习技术的整个实用链条。机器学习的进步,既提升了广告推送的效率,从而取悦了广告主;也提升了搜索结果的精度,从而取悦了消费者。IBM在医疗、交通等场景未能实现的良性循环,在广告场景却比较顺畅地实现了。
2016年以来,随着美国和欧盟的消费者隐私保护立法进程的深入,互联网公司不得不配合进行自律式监管,其中影响最大的两个举措就是Apple修改IDFA(广告提示符)政策,以及浏览器厂商纷纷禁用第三方Cookie。上述两个举措均会导致广告平台或广告代理商追踪用户身份的难度提升,从而既无法精准地推送广告,也难以准确衡量广告转化率。
迄今为止,Alphabet的广告收入增速没有受到实质性影响,其管理层也不认为用户隐私政策将对自身的广告业务构成重大约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Alphabet通过前瞻性的技术研发,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用户隐私保护的影响。
最典型的例子是2019年宣布、2021年开始实施的Google Privacy Sandbox方案。该方案的核心是改变广告推送人群,不再追踪个体浏览行为,转而追踪有类似浏览习惯的群体,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隐私。Google宣称,Privacy Sandbox的最终目标是废除浏览器端的第三方Cookie和安卓端的广告提示符,同时尽量不影响广告推送精度。虽然监管部门和外部开发者对此充满疑虑,但是我们应当承认,Google提出了目前对于解决互联网用户隐私问题比较全面、有实用价值的解决方案。
Google Privacy Sandbox应用了多种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其中最重要的算法之一是“群体联盟学习”(Federated Learning of Cohorts),原理是将浏览相同内容的用户“混合”起来,赋予一个群体ID,从而在不泄露个体身份的情况下进行基于兴趣的广告投放。听起来非常庸俗、缺乏美感,但正是这种“庸俗”的技术应用,支撑着那些更远大、通向“星辰大海”的前沿技术研发。(注:该算法其实并不符合“联盟学习”的定义,可能是因为Google在开发过程中改变了技术路线。)
浏览器端的Google Privacy Sandbox时间表
资料来源:Google Privacy Sandbox官网
与此同时,鉴于搜索广告在全球广告市场的份额已经见顶,Alphabet一直在探索更多场景、更多形式的广告投放,其中首要的是基于地理位置(LBS)的投放。上文提到过,新冠疫情彻底改变了美国消费者的习惯,零售商因此更加追求“全渠道零售”,试图整合线上线下供应链和履约能力——无论是吸引到店消费,还是进行“线上下单、线下/路边提货”,乃至提供到家配送服务,都离不开地图等LBS应用;而美国最流行的地图应用只有Google和Apple。
按照Alphabet管理层的说法:“我们计划向中小企业提供……在线上和线下获客之间无缝切换的能力,范围应该大大超越它们的邻近地区。”在实体商品方面,Google允许零售商标注存货状态(是否有货)、送货选择(是否支持配送到家/路边提货);在服务方面,Google在部分地区开放了订票、酒店预订乃至服务预约功能。这些功能,在中国大多被归类于“本地生活服务”,看上去似乎缺乏技术含量。事实恰恰相反,Google通过强大的算法技术(包括但不限于大数据、机器学习),提高了商家与用户的匹配效率,从中获得了大量收益。
2021年5月,Google先后与Shopify和Square两个美国最大的零售行业SaaS服务商签署合作协议,允许其客户更方便地在Google展示商品广告,同时也开放了一些数据接口。今后,对于小型本地商户而言,在Google上标记地点、展示货架、显示服务状态可能会更加容易,只要通过Shopify和Square的系统一键同步过去就可以了。这个举动彰显了Google建立“开放式零售生态系统”,从而在美国零售广告市场获得更多份额的决心。对于传统的本地广告投放渠道,例如本地报纸、本地电视台、户外广告而言,则绝不是什么好消息。
Google Maps可以提供本地商户的细节和评分
另一个重要方向是视频广告。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视频(含短视频)都是用户时长增长最快、广告开支比例上升最快的在线内容品类。Alphabet旗下的YouTube不但是美国最大的移动视频APP,而且在OTT市场的渗透率也仅次于Netflix。近年来TikTok的兴起,虽然严重影响了Facebook和Instagram的用户和收入,但是对YouTube几乎没有影响。YouTube广告收入占据Alphabet总体收入的比重,也从2017年的7.3%上升到了2021年的11.2%;我们估计,如果把YouTube付费会员收入也计算进去,它的收入贡献比可能达到15%。
YouTube广告业务有两个重要的增长驱动力:第一是随着它不断深入“大屏”(OTT)场景,它也在逐渐侵蚀有线电视的市场份额,甚至成为了“大屏端”最重要的广告平台;第二是通过提升算法、推出更多形式的“直接响应”(Direct Response)广告,从而进一步提升效果广告的精度。附带说一句,YouTube也推出了“直播带货”功能,而且效果明显好于同样推出了带货功能的Instagram。
相对于基于文字的传统搜素广告而言,视频广告的算法复杂性本来就更高;何况YouTube贴片广告在播放几秒之后就能够由用户主动跳过,从而对广告推送精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没有强大的算法技术,就无法在用户体验和广告收入增长之间达到平衡。现在,YouTube的一个技术投入重点是提升OTT端的广告效果衡量能力——用户有没有注意观看,有没有尝试进行互动(包括在移动端的互动)?这是传统电视广告完全无法做到的,也是广告主将预算不断转移到YouTube的原因。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Alphabet CEO Sundar Pichai在2021年四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所说的:“在提升搜索、地图、YouTube等信息产品的使用价值的过程中,对人工智能的投资将是一个关键因素。”准确来说,此处的“人工智能”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通常所谓的机器学习、大数据、生物识别、物联网等技术。它们从Alphabet平台每天产生的海量数据当中获取养分,然后反过来提高平台的运营和商业化效率。
Alphabet没有将强大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用于太空探索或火星移民,这一点可能会让国内的一些“硬科技”爱好者失望;当他们意识到Alphabet的主要业务与国内的腾讯、百度之流没有本质性区别的时候,可能会更加失望。然而,正是这些平淡无奇、接近日常生活的广告业务,在过去十年推动Alphabet的营业收入增长了6倍、营业利润增长了7倍,使得它得以手握1396亿美元的现金,每年花费87.1亿美元的研发费用(均为2021年数据);仅仅Google Research这个“前沿研发中心”就雇佣了2297名科研人员。
在2021年度报告中,Alphabet管理层写道:“在历史上,不走寻常路的精神一直驱动着我们,鼓舞我们去解决重大问题,投资于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疯狂的想法。”很多公司都有过“不走寻常路的精神”、投资于“疯狂的想法”,其中绝大部分都失败了。IBM Watson就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可惜它未能治好癌症。Alphabet与这些失败者的最大区别在于拥有消费互联网这个永不枯竭的现金来源,从而能为“解决重大问题”投入无穷的弹药。否则,它的理想就永远只能停留在理想阶段。
一个严肃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硬科技”公司?
从2019年A股科创板成立开始,“硬科技”成为了国内资本市场的热门名词。2021年以后,“硬科技公司”往往被拿来与“互联网公司”做对比——前者专注于基础研发和重大发明创造,后者则只想着从流量生意里捞钱;前者是智力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后者只能算得上人力密集和资本密集而已;前者代表着人类社会真正的发展方向,而后者很可能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段弯路。
究竟什么是“硬科技”?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2021年4月修订),科创板上市公司应该属于以下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与此同时,限制金融科技、模式创新类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当中,人工智能是无可争议的宠儿,炙手可热的程度可能仅次于半导体和集成电路。提到人工智能,大部分投资者马上就能想到两家公司的名字:已经在港股上市的商汤科技,以及申报科创板但尚未过会的旷视科技。在一级市场赫赫有名的“AI四小龙”当中,它们是最早申报上市的两家,显然符合资本市场对“硬科技”的定义。
商汤和旷视都是比较纯粹的To B公司,产品应用范围还比较狭窄,营业收入有限,所以均处于亏损状态。2021年,商汤的经调整净亏损率高达30.2%;旷视尚未披露2021年度数据,但是上半年其扣非净亏损率高达138.8%。投资者对这种巨额亏损的意见并不一致,有人认为“硬科技公司”就是应该在早期多亏钱,有人则希望尽快缩小亏损并提出盈利路线图。在2021年以前,国内资本市场的对人工智能企业的风险容忍度还是比较高的,进入2022年以后则出现了明显的收缩。
从招股书及财报披露数据看,旷视和商汤的客户集中度都比较高,对大客户比较依赖——2021年上半年,旷视前五大客户贡献了25%的收入,商汤最大的一个客户就贡献了23%的收入。此现象很好理解:这两家公司均未直接掌控应用场景,既缺乏消费级客户,也缺乏中小企业客户;至少在现阶段,它们必须先把自己的技术解决方案卖给大型企业,由后者负责应用场景和客户服务。事实上,很多“硬科技公司”目前实践的都是这种商业模式。
那么问题来了:假设一家拥有类似技术研发能力的公司,恰好也有庞大的消费级业务,而且可以将自身的研发成果直接应用到消费场景中,那它还算不算硬科技公司?
这样的公司是存在的。本文讨论的全部公司,尤其是Alphabet、Amazon和Meta,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方面有大量研发成果,而且直接运用于内容推荐、商品推荐、广告推送和广告效果衡量。Microsoft也有较强的人工智能技术,主要应用于Azure云服务。Apple在这个领域的存在感稍弱一些,但是iPhone用户应该都对Siri非常熟悉;在地图和流媒体服务场景,Apple也需要广泛地应用人工智能。别误会,上述科技巨头当然会使用外来技术,并与外部公司或科研机构进行研发合作。但是,它们的核心技术以自主研发为主,或者通过收购完成“自研化”(Amazon和Apple尤其擅长这种操作)。
事实上,国内的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巨头,出于商业上的考虑,一直在大力研究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2017-2020年字节跳动广告业务的迅猛增长,以及同一时期淘系电商GMV及广告收入的稳定提升,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算法推荐精度的提高;腾讯除了在广告业务上需要机器学习,在游戏业务上也需要(尤其是PVE方面);百度则在无人驾驶技术上投入重注,这显然个技术高度密集的业务。
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何上述互联网巨头没有被称为“硬科技公司”,反而经常被列为硬科技的对立面呢?是因为它们在消费端太成功了吗?是因为它们直接介入了应用场景吗?还是因为它们的业务规模实在太大,外界难以准确辨认哪些部分的技术含量较高?无论是哪个原因,它们都是因为自己“过于成功”而受到惩罚。
2021年,商汤和旷视的研发费用之和约为48亿元(注:旷视未披露年度数据,按上半年数据的两倍估算);美团、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的研发费用分别是这个数字的3.5倍、5.2倍、10.9倍、12.1倍。当然,研发费用是一个局限性很强的财务指标,不能单独代表企业的研发实力;而且互联网巨头的研发团队需要分散到许多个不同的方向。然而,只要腾讯或阿里将其研发资源的十分之一投向人工智能方向,就足以与两家“硬科技公司”的投入旗鼓相当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互联网巨头的硬科技水平会弱于纯粹的“硬科技公司”。
肯定会有人这样反驳:“但是互联网巨头研究硬科技仅仅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垄断地位,与整个社会无益。只有纯粹的硬科技公司会向全社会输出技术。”很可惜,这种臆想是错误的。互联网巨头也会向外部输出“硬科技”研究成果,不是因为它们的心肠有多好,而是因为这是一门能赚钱的生意。
“机器学习即服务”(Machine Learning as a Service, MLaaS)是云计算领域的一个新方向,也是各大公有云平台的兵家必争之地。根据《福布斯》杂志预测,2020年全球MLaaS市场规模即已达到73亿美元,2024年将增长到306亿美元。
简而言之,就是由科技巨头从云端向客户提供成套的机器学习工具,这样客户就不用自己研究、自己部署相应技术了。例如,Amazon机器学习服务可以帮助客户处理自然语言、发布聊天机器人、建立时间序列预测模型、进行图形和视频分析,以及文本/语音转换服务——几乎就是机器学习目前所具备的一切功能。
进一步说,以云服务的方式向大量客户提供标准化的机器学习工具,有助于大批企业和组织享受到最新的技术进步,从而减少技术上的不平等。就像Alphabet在2021年财报中所说:“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均衡器(Equalizer)。”如果我们不是以互联网的方式,而是以传统软件服务的方式去交付机器学习能力,那么必然只有最大的一些组织有能力享受。难道硬科技成果不应该最快速地服务于最大多数人吗?
四大“机器学习即服务”平台功能对比
资料来源:Alexsoft
根据Alexsoft的分析,在全球最领先的四大MLaaS平台当中,Amazon和Microsoft并列第一,功能最完善;Google次之,进步势头很快;IBM Watson又次之。我们不得不再次感叹,在人工智能方面,IBM起了一个大早,却赶了一个晚集。由于收入和利润多年停滞不前,IBM已经出售了曾经最重要的Watson Health业务,我们很难指望它能在MLaaS领域与三大互联网巨头展开平等的竞争。讽刺的是,按照部分国内投资者的标准,IBM肯定算一家“硬科技公司”,而Amazon肯定不算。
美国科技巨头也惦记着本地零售,而且力争将其作为突破口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巨头因为近场电商的押注而饱受争议。所谓近场电商,就是消费周期较短、对即时性和本地化要求较高的电商业务,包括餐饮外卖、到店、生鲜、日用食杂、买药、社区团购等;与线下实体的近场零售结合起来,就是所谓“本地零售”。美团、阿里、拼多多、京东均在此投入重兵,百度、滴滴也有过一定程度的参与。
问题在于,对本地零售市场的争夺恰恰是从美国开始的,阿里、美团、京东的举动均带有对Amazon的强烈模仿色彩。截止2021年底,Amazon已经在美国和英国建立起比较完整、覆盖面较广的生鲜和食杂电商体系。Alphabet虽然尚未全面下场,但也在跃跃欲试地尝试各种可能性。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科技巨头也惦记着线下零售的生意,并且将其作为持续改造传统经济的突破口;这丝毫没有损害它们的“技术含量”。
Amazon全面进攻近场电商:以生鲜和日用食杂为核心
2017年,Amazon以137亿美元收购了以有机食品著称的Whole Foods Market,标志着这家电商巨头全面进军线下零售市场。截止2021年底,Amazon在整个美国拥有599家实体零售店,其中有503家属于Whole Foods品牌(比收购之前增加了100多家);Amazon的生鲜电商业务也主要是以Whole Foods为支点组织起来的。
Whole Foods承载了Amazon本地零售的半壁江山
收购Whole Foods不是Amazon进军近场电商和实体零售的开始,更不会是结束。早在2015年,Amazon就在美国部分地区推出了Treasure Truck会员快闪店,一开始仅支持线上购买、线下提货,后来逐渐演变为实体店;目前该服务已经扩展至美国本土绝大部分地区。同年,Amazon Books实体连锁书店开业,不过经营情况不甚良好,已经于2022年开始逐渐关闭。就在收购Whole Foods的同时,Amazon Fresh生鲜电商服务也开始运营,并于2020年发展出了实体连锁店。
相对于价格高昂、强调环保和食品质量的Whole Foods,Amazon Fresh明显更接地气一些,定位更接近于社区超市。二者都是彻底的自营业务,由Amazon掌握整个供应链和物流体系。接下来,Amazon的战略可能是以Whole Foods主攻高端市场,尤其是到店消费和大城市的即时配送服务;Amazon Fresh主打低端市场,尤其是中小城市或时效性较弱的配送服务。与国内的服务对比,前者比较类似盒马鲜生,后者更接近淘鲜达、京东生鲜。
在历史上,与中国相比,美国的电商渗透率较低,用户习惯于在本地实体店购买日用食杂。其中有很多复杂的原因:美国地广人稀,人工成本高昂,传统零售行业发达,用户习惯很难在短期内改变。然而,2020-2021年的新冠疫情,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消费习惯,至少让近场电商的进程加快了3-5年。咨询公司Dunnhumby的年度调查显示,疫情期间,在日用食杂采购方面,美国人对“速度”和“安全性”的要求大幅提升,而Amazon在这两方面均能获得高分;对“价格”的敏感性有所下降,而这曾经是Amazon的一个软肋。结果毫无悬念:Amazon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当一个美国消费者于2020年上半年首次尝试Amazon Fresh或Whole Foods配送服务时,他可能只是不想暴露在公共场合,又或者因为实体店排起了长队;在几个月的使用之后,这就变成了一种习惯。值得一提的是,在疫情高峰期,与大部分实体零售商一样,Amazon也出现过严重的断货现象,配送周期也一度大幅延长。这促使了Amazon进一步加强对供应链和履约能力的投资,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此类现象再次发生。
至于Amazon从2018年来一直大力尝试,并于近期推广到Amazon Fresh线下店的“无人无现金零售”模式,也在疫情期间焕发了生命力。为了保持社交距离、避免暴露,许多消费者乐意选择自动化的结算服务。一般超市的无人结算柜台操作流程非常繁琐,往往引发了更严重的排队;Amazon却可以在部分门店做到“拿起就走”,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不言而喻。但是,在疫情平息之后,无人结算的吸引力能否保持下去,还有待观察。
那么,Amazon在日用食杂行业的扩张,是否会导致传统日用超市大批倒闭,直至引发让许多零售业人士恐惧已久的“零售末日”(Retail Apocalypse)——除了电商之外的零售渠道全部垮掉?至少目前还远远没到那一步。2020-2021年,在美国日用食杂零售偏好指数(RPI)当中排名前14的,只有Amazon以电商业务为大本营,其余全是老牌连锁超市。
在疫情期间,除了Amazon之外,Target、Fry’s Food & Drug等传统零售品牌的上升速度也很快,提供配送或路边提货服务的超市也越来越多。显然,Amazon不是终结者(至少现在不是),而是鲶鱼,推动了整个日用食杂零售行业的效率提升。
事实上,Amazon在本地零售方面的投入,既是进攻性的,也是防御性的;防御的目标就是老对手Walmart。虽然后者在市值、利润以及电商业务规模方面被前者远远地甩开了,但是它在全美拥有5339家线下门店,是前者的近十倍;截止2021年底,后者在全美拥有150个配送中心,高于前者的110个。Amazon在美国消费者中的总体渗透率为65%,而Walmart线下店则是63%,Walmart线上业务也有37%——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Walmart从来就没有真的死掉。
对于Walmart来说,最大的翻盘机会在于近场电商,尤其是日用食杂。Walmart及其旗下的Sam’s Club在美国日用食杂零售指数的排名都比较高,在“价格”和“数字化”两项的得分尤其高。等到疫情平息,美国消费者对“速度”的要求下降、转而更重视“价格”时,Walmart可能会拿走更多的市场份额。无论如何,Walmart庞大的实体渠道和配送能力,本身就是对Amazon的不容忽视的威胁。
如果Amazon竟然拱手让出先发优势,坐视Walmart夺取生鲜日用电商的领导地位,那么接下来动摇的可能就是传统零售电商业务。根据Jungle Scott的统计,2021年,有7%的Amazon第三方商家已经在Walmart.com开店,39%计划在Walmart.com开店。商家总是跟着趋势走,用户又会跟着商家走;如果不想失去用户,最好就是从根本上扼杀趋势。因此,即便近场电商业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赚不到钱,Amazon也必须对此领域进行“防御性扩张”。
对比国内电商市场,我们会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阿里、京东均在2015-16年开始线下零售尝试并提出“新零售”概念;2017-19年,美团、每日优鲜、叮咚买菜、盒马鲜生、京东生鲜等围绕“买菜”展开了激烈竞争;
2020年,在疫情的大环境下,生鲜电商和社区团购都迎来了快速发展。如果在地广人稀、传统零售行业强势的美国,Amazon这样的科技巨头都敢于大举押注于本地零售,那么在条件更优越、更有利于互联网公司的中国,近场电商成为巨头必争之地就很容易理解了。
Alphabet和Meta以自己的方式染指本地零售
Google (Alphabet)在历史上推出过无数失败的产品和服务,往往被外界戏称为“产品坟场”。有些失败的服务广为人知,例如Google Video、Google Music、Google Buzz;有些则远离公众视线。很少有人记得,Google曾经在2013年推出过名为Google Express的当日达/次日达配送服务,一开始仅限于旧金山和硅谷,此后逐步扩展至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等地。如果在2013-2018年之间,你曾经在这些城市看到过打着Google商标的汽车,那么它们多半隶属于Google Express自有的配送车队。
与Amazon不同,Google既没有自营电商,也没有电商平台业务。它的计划是与大型零售企业(包括Walmart、Target、Costco等等)以及本地商超合作,通过Google平台接收订单,以算法自动分配到最近的线下零售店,然后由自营车队就近配送。为了与Amazon竞争,Google Express的会员费被刻意设置为略低于Amazon Prime。遗憾的是,这项业务从来没有获得足够的用户和订单,于2019年黯然收场。
一辆Google Express配送汽车
Google Express的失败,让Alphabet管理层意识到:在缺乏自己的电商业务的情况下,单纯依靠为第三方线下商家提供配送服务来染指电商市场,是不可能成功的。Google Express想做的主要是近场电商的即时配送(以当日达为主),这项业务对于供应链整合的要求太高了,用户体验很容易变得很差。从那以后,Alphabet的战略变成了只做广告、不做交易环节,满足于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传递信息。
在Google平台,实体商家可以通过Google My Business注册自己的档案,从而出现在Google搜索结果和地图上。疫情期间,通过Google获客对商家而言变得更加重要,Google也顺势诱导它们登记更多信息,包括电话、服务状态、社交媒体账号,以及上文提到的存货状态、配送服务等。2021年以来,Google大幅简化了商家修改自身档案的流程,并且开放了Shopify和Square的数据接口。结果就是,消费者在寻找本地商家和配送服务的时候,对Google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了。
Amazon建立了庞大的自营供应链、线下场地和配送网络,从而实现标准化的快速交易闭环,这是近场电商;Alphabet没有任何供应链和物流能力,仅仅通过信息和算法提高用户的本地购物效率,这也可以视为一种近场电商。不同之处在于,Amazon可能夺走很多“小商小贩”的生意,而Alphabet则是在为“小商小贩”撮合生意,后者更容易获得舆论同情。然而,前者通过垂直整合实现的高效率、强用户体验,是后者所无法比拟的。
Google My Business在疫情期间变得更加重要
目前,Alphabet显然没有重启电商业务的打算;鉴于近场电商的竞争已经比较激烈,就算现在入局恐怕也晚了。它只能另辟蹊径,想办法在提高信息质量上做文章:
Google Street View(VR/AR街景服务)可以提供商户内部视角,引导用户实现虚拟逛店,而且与Google Maps无缝衔接。Google宣称,提供全景图片和导览能够使用户关注店铺的几率提升一倍,使购买可能性提升29%。
Alphabet正在与Adobe展开长期合作,希望将Photoshop、Illustrator等设计工具搬到浏览器和移动端;最终目的是鼓励个人和商家创作更多的专业图形内容,提升消费者的直观感受。
YouTube的本地化趋势也很明显,尤其是在YouTube Shorts(短视频)方面。Alphabet通过算法鼓励本地商家进行视频广告投放,将Google搜索、Google Maps和YouTube结合起来,吸引邻近用户消费。
在2021年四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上,Alphabet管理层估计,在后疫情时代,旅行、休闲等消费活动将取得有力的反弹——2021年9-10月,在Google对“旅行规则”(travel rules)的搜索数量同比上升了六倍。这很可能是Alphabet相对于Amazon的一个重要强项,因为前者与大批酒店、旅行社、航空公司和旅游景点有合作关系,能提供从航班预订链接到门票预购的一系列服务;而后者虽然也有一些旅行和休闲行业的商家入驻,但是总体上不重视非实体商品交易。
Google Street View与Google Maps的无缝连接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重要推论:日用食杂等“本地实体商品交易”的数字化,必然会通向酒店、旅行、休闲娱乐等“本地服务交易”的数字化。国内互联网从业者应该很好理解,“到家服务”和“到店服务”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未来有一天,Amazon是否有必要加注于近场服务?应该如何加注?没有人知道。这就是互联网行业的撩人之处,一切皆有可能。
最后,我们也不能完全忽视Meta在近场电商领域的存在,尽管它的存在感远远弱于前面两家巨头。广告主正在对Facebook失去兴趣,因为它的用户年龄偏大、内容互动性太差;但是Instagram仍然颇具吸引力,2016年推出的Stories、2021年推出的Reels功能进一步提升了它的内容多样性。在疫情期间,美国线下商户在Instagram进行的营销活动有提升的趋势,其中既包括硬广告、软广告(本地KOC)投放,也包括基于内容的运营。与Google一样,Instagram和Facebook均允许商家基于地理位置标签进行广告投放。
在历史上,Meta曾多次尝试建立“电商交易闭环”,最近一次是2019年重建Instagram电商团队。在2021年四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Mark Zuckerberg将电商列为2022年的七个重要投资方向之一。然而,鉴于Meta一贯薄弱的执行力,我们无法对此抱有太大希望。
被管理层寄予厚望的Instagram直播带货,实际效果平平,销售额与中国的直播带货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也许在时尚、美妆等特定品类,Instagram还能做出一些交易额;在其他品类则希望渺茫,在生鲜、食杂等近场品类就更不可能了。投资者对此心知肚明,没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奢望。
Meta手中唯一一张王牌是所谓“社群通信”:WhatsApp是美国最重要的即时通信APP,Facebook和Instagram内部的信息功能也有大量用户。Meta管理层企图将这些通信功能打造成商家与消费者沟通的渠道,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动客服;还企图进一步介入企业内部,打造Slack或国内的钉钉、企业微信那样的企业通信工具。平心而论,前一个目标还是有可能做到的,因为Google难以为商家和消费者提供即时交流渠道;后一个目标离Meta的能力圈太远,而且不是特别诱人。
在争夺本地零售的蛋糕之前,Meta还必须克服用户隐私保护的障碍:Apple关闭广告标识符已经严重影响了它的广告业务,而Android做出类似举措只是时间问题。即使不考虑算法技术水平的差距,上述隐私政策对Meta的影响也远高于对Google的影响,因为后者可以依靠用户主动输入的关键词进行推送,还拥有强大的地图应用;前者的本地内容推送和效果衡量则会受到更大的打击。无论如何,Meta当前的战略聚焦于虚无缥缈的“元宇宙”愿景,在本地零售方面最多只能维持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找不到像样的突破口。
美国科技巨头真的抢了线下小型零售商的饭碗吗?
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善良的人们总是会担心科技巨头的扩张会抢走中小企业的市场份额;尤其是在本地零售领域,线下零售从业者的利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哪怕最后的赢家不是Amazon,而是Walmart或Kroger等传统巨头,对本地小型零售商也不会是什么好事。在美国,确实有许多非营利组织在呼吁遏制科技巨头在这方面的扩张。例如,前面章节曾经援引的ILSR研究报告就认为Amazon已经演变为“收费公路”,甚至应予以分拆。监管者是否应该顺应这种呼吁?
我们的观点与此相反。首先,任何企业(包括小企业)存在的目的是为客户提供服务;企业是为客户存在的,而不是相反。如果一项商业模式的变革确实有助于提升消费者效用,那么就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目前美国最大的六个食杂电商平台,分别采取了纯会员模式、混合模式、非会员模式,对最低配送金额和配送费的规定也有明显差异,从而给了消费者更好、更灵活的选择。难道为了保护小型线下零售商的利益,就应该剥夺消费者享受这些权益吗?
美国主流日用食杂电商平台的服务条件
资料来源:Clark.com
其次,并不是所有小型线下零售商的利益都受到了损害。《大西洋》杂志在2017年撰文指出,零售电商的兴起导致了美国人购买服装的开支下降,餐饮、旅行消费则有所上升,对餐馆和酒店质量的要求也提高了。这就是所谓的“体验经济”(Experience Economy):消费者不再愿意为了标准化产品支付高价,而更乐意为定制化的服务付钱。近场电商可能导致同样的后果,在关闭的本地零售商的遗迹上,一批新的餐饮、美业、休闲娱乐服务商将成长起来。
与此同时,本地日用品和农产品生产商反而会受益。市场研究机构Mass Market Retailer的调查显示,在Amazon Fresh线下门店出售的啤酒SKU当中,只有8%属于全国性SKU(在所有门店均可买到),剩下的都是地方性品类;葡萄酒则只有12%属于全国性SKU。有趣的是,Amazon Fresh门店的平均SKU数量却远远低于传统连锁零售店——也就是说,前者比后者更加本地化,更加依赖垂类和中小型生产商。
这种情况其实很好理解:在线下,为了与传统零售商形成差异化竞争,Amazon等互联网巨头采取了扶持中小品牌和私有品牌(生产商贴牌)的策略,从Whole Foods开始就是如此;在线上,由于电商货架的深度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能够容得下多个品牌,还没有传统连锁商超的高昂入场费,中小品牌也获得了较大的空间。
这种现象在服装、美妆等非近场电商品类也是成立的,所以近年来美国涌现出了一大批DTC (Direct-to-Consumer)品牌,它们完全立足于线上渠道(包括独立站和平台),对传统全国性品牌构成了无休止的冲击。在此,我们更能理解Alphabet提出的“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均衡器”这一说法的正确性。
况且,不是所有科技巨头都像Amazon一样致力于整合零售渠道和供应链。上文提到,Alphabet基本不涉足零售交易环节,Meta也只有一个规模较小的电商业务;在近场电商领域,它们的商业模式基本完全依靠广告,也就是为本地商家获客和促成交易。在2020-2021年的疫情时期,美国消费者的出门购物欲望受到抑制,如果没有互联网的支持,线下商家的日子只会更难过。
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于2021年进行的调查显示,美国小企业有80%在数字平台(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官网等)发布产品和服务,有75%通过数字平台完成销售;如果面向消费者的小企业缺乏线上渠道,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可能下降一半左右。
此外,有80%的小企业认为Facebook有助于它们获得新客户,56%认为Facebook有助于增加销量,甚至有32%认为Facebook是自己“建立生意的基础”——这种企业一般要么采取纯线上销售,要么是所谓“鼠标加水泥”商业模式;它们广泛活跃于Amazon、Google、Instagram等一切大型平台。
还记得前文提到的一组数据吗?2021年10月的感恩节前夕,在Google Maps搜索“我附近的礼品店”的数量同比上升了70%。用户也不必担心跑到店里却买不到礼品,因为现在Google允许商家设定库存状态:3件以上为“有货”(In Stock);1-2件为“供货紧张”(Limited Stock);大件或限量商品可以设定“仅供展示”(ODO);当然也可以是“无货”(Out of Stock)。虽然Google已经不再提供配送服务,但是目前在Google Shopping成交的本地订单当中,有1/4使用了Google提供的“路边提货”标签。
Alphabet究竟对美国本地零售市场有多大的推动作用?没人知道,反正很大。
我们有理由相信,从线上信息渠道受益最多的,是那些边缘化的小微企业或初创企业,因为它们无法负担除了线上推广之外的任何推广形式。而且,线上推广不一定需要花钱,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内容运营,或者简单地将店铺登录到各大平台。2021年,有61%的美国消费者会通过各种线上渠道发现本地小企业,其中半数以上是通过“朋友的社交媒体帖子”或地图搜索进行。在Quora问答平台,你可以找到数千个关于“如何零成本地在Instagram/TikTok/Twitter进行本地推广”的回答。不花钱的推广,往往不好用,但对小微企业而言够用了。
随着年轻消费者逐渐长大,互联网平台对小型线下零售商的帮助作用会进一步提升。中小企业SaaS服务商QuickBooks的调查显示,“千禧一代”(80后/90后/00后)消费者有69%依靠线上信息进行线下消费,比例远高于全体消费者。他们使用的当然不仅限于“五巨头”旗下的平台,还包括Pinterest、Discord这样的“特色社交媒体”,以及Yelp!、OpenTable这样的垂类信息平台。在大众点评选餐馆、用高德或百度地图找地点、用美团或口碑团购券进行结算——这种消费路径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世界上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都很常见。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科技巨头改变了零售行业的版图,也就是改变了利益分配格局,在此过程中必然有大批小型线下零售商受损。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类似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这就是经济学上著名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概念。按照Joseph Schumpeter的论断:“国内和国外新市场的开放,以及在手工业和工厂内部发生的组织进化,形象地展示了产业突变如何不停地从内部革新整个经济结构,不停地摧毁旧的经济结构,也不停地创造新的。这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是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现象。”
监管者的任务不是打断“创造性破坏”,而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足够的补贴、支援和转型训练。无论有没有科技巨头,在任何时代,中小企业的破产率本来就很高,盈利能力本来就很低。静态地保护中小企业不受技术进步的伤害,无异于刻舟求剑。只有两件事情是必须的:保证新的中小企业不断诞生;保证在竞争中破产的中小企业主具备重新站起来的能力。
美国的科技反垄断:雷声很大,雨点较小
作为全世界最早通过反垄断法的国家,美国监管者对于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巨头”一直比较警惕。从计算机商用化开始,信息科技行业的历代领军者都是反垄断行动的重点照顾对象:1969-1982年,美国司法部致力于通过诉讼分拆IBM;1998-2004年,美国司法部进行了旨在分拆Microsoft的诉讼。这两起诉讼均以庭外和解告终,但是IBM和Microsoft的市场支配地位均在诉讼过程中出现严重下滑,这大概不是巧合。
从2017年起,美国舆论界关于对新一代科技巨头发起反垄断行动的呼声不绝于耳。2010-21年,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对除了Microsoft之外的“四巨头”进行了反垄断调查,并于2021年6月推出了六个针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法案。同年7月,拜登总统签署第14036号行政命令,指导行政部门对科技巨头的并购、数据收集等行为施加更严密的监视。同一时期,美国联邦法院系统也收到了针对多个科技巨头的起诉。上述大部分消息均得到了国内媒体及时、密集(但并不一定全面)的报道。
然而,进入2022年,我们惊异地发现:美国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行动,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层面,都呈现“雷声大、雨点小”的态势,美国舆论对反垄断的关注程度也大幅降低。虽然美国监管者不会放弃,但要在短期内对科技巨头施加有效的打击,难度恐怕很大。
立法行动:八个反垄断法案,仅有两个通过概率较高
2021年6月,作为长达两年的针对科技巨头的调查的阶段性成果,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发布了六项反垄断立法草案。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针对“主导性平台”,覆盖范围需满足如下条件:
满足美国本土MAU(月活用户)5000万以上,或本土商业月活用户10万以上;
持有者或控制者的年销售净额或市值超过6000亿美元;
在该平台所经营的业务上是一个关键市场参与者。
可以看到,“六项法案”只针对消费互联网公司,因为企业服务公司难以满足MAU的阈值;只针对以美国为大本营或重要市场的公司,因为用户数量以美国本土为准;只针对在商业上非常成功的公司,因为对销售额和市值的要求极高;只针对在消费互联网业务上非常成功的公司,不覆盖那些跨界试水或玩票、不算“关键参与者”的公司。毫无疑问,在当时同时满足上述条件的“主导性平台经营者”仅有Apple、Amazon、Alphabet、Meta四家;Microsoft不一定满足。
除此之外,国会两院议员还在2021年提出了另外两个法案,适用范围与前六项法案不同,但也是面向科技巨头:一个旨在对应用商店经营者进行监管,一个旨在限制大公司的并购行为。我们可以将它们一并统称为“八项法案”。本届国会还存在大量其他反垄断法案,但是它们的严肃性不高、受到关注较少,通过的可能性很低。我们主要需要讨论的就是“八项法案”。
“八项法案”的文本非常复杂,参众两院审议的版本又多有不同,但是立法目的是比较一致的,即防止科技巨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保护其竞争对手和客户。具体措施如下:
American Choice and Innovation Online Act: 主导性平台不得优待自营产品和服务;不得限制自身用户经营与自己竞争的业务的能力;不得歧视商业用户以损害竞争;不得施加“其他歧视行为”。该法案对“其他歧视行为”的技术细节进行了深入描述。
Ending Platform Monopolies Act: 主导性平台的经营者,不得经营平台业务之外的业务线,以避免利益冲突。简而言之,平台必须与非平台业务分离,像Amazon这样既有第三方业务、也有自营业务的公司首当其冲。
The ACCESS Act: 主导性平台必须保持数据接口技术格式的透明性,允许用户在不同的平台之间传输和使用自己的数据,实现不同平台的“互操作性”。平台可以为这种“互操作性”收取合理的费用。也就是说,平台不能再独占数据、阻碍用户转移到竞争对手那里。
Platform Competition and Opportunity Act: 主导性平台的经营者,在进行商业性的并购或投资行为前,必须事先证明这种行为不会损害市场竞争。这无疑是将并购反垄断的举证责任倒置了,就连纯粹的财务性投资也会受到影响。
Merger Filing Fee Modernization Act: 大幅提高执法机关对公司并购活动收取的审查费用,并要求根据CPI逐年调整费用。不过,调整之后的审查费用对于科技巨头而言还是很低,本法案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State Antitrust Enforcement Venue Act: 赋予各州检察长广泛的权力,可以决定在哪个联邦地区法院提起反垄断诉讼,防止科技巨头将诉讼转移到对自己有利的地区审理。不过,鉴于美国重要的反垄断诉讼一般是由联邦发起,该法案的实际效果也有限。
The Prohibiting Anticompetitive Merges Act: 禁止一切导致市场份额过度集中,或价值高于50亿美元的并购。美国司法部或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有权直接拒绝并购,无须等待法院判决。对于过去的并购,可以进行追溯性审查并勒令拆分。可以看到,这项法案相当严苛,几乎要从根本上禁止大规模并购行为。但是,正因为它过于严苛,在国会的支持率很低。
Open Apps Market Act: 在美国拥有5000万以上用户的应用商店,不得对开发者施加排他条款,不得阻止开发者与用户直接联系,应该允许用户在本平台选择和安装第三方应用商店。这个法案当然是冲着Apple来的,尽管Alphabet也会受一些影响。
这一连串的立法,让人看着血脉贲张,实际又有多大的通过可能性呢?很遗憾,恐怕只有2-3个有希望通过。美国的联邦立法流程是先由两院的相关委员会(以及其下属的小组委员会)审议,例如上述八项法案均由两院司法委员会(Committee of Judiciary)审议;若通过,再提交全院审议;在两院均表决通过的情况下,若法案文本有冲突,还要成立两院协商小组,协商结果还要再由两院通过一次;最后提交总统,签署成法。上述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均可能导致法案夭折。
美国的联邦立法流程
资料来源:Friends Committee on National Legislation
“八项法案”目前处于立法流程的什么阶段?其中只有三个在两院司法委员会获得通过,但迄今均未提交全院审议;三个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获得通过,也未提交全院审议;一个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获得通过,同样未提交全院审议;还有一个尚未通过任何一院的司法委员会。从联署议员人数、是否获得了两党议员同时联署,以及在委员会的投票结果看来,我们认为其中仅有两个法案通过概率较高,而且恰恰是不太重要的法案;两个法案通过概率中等;剩下的通过概率均不大。
鉴于“八项立法”均是主要由民主党推动,而民主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的处境不容乐观,所以一旦共和党赢得选举,恐怕就意味着“八项立法”被无限期搁置。拜登总统目前也尚未对“八项立法”进行公开表态,虽然一般认为他支持反垄断,但这似乎不属于他的优先事务。按照国会官方时间表,本届国会将于2022年8月进入休会期,休会结束之后就是激烈的中期选举。这就意味着如果“八项立法”未能在7月以前被列入两院的全院议程,今年之内就不太可能得到审议了。
“八项立法”状态:蓝色为有利,绿色为中等,橙色为不利
美国国会的反垄断立法之所以雷声大、雨点小,除了因为共和党强烈反对之外,更深层的原因是美国民众的注意力焦点已经不再是反垄断。本次中期选举的热门议题包括通货膨胀、潜在的经济衰退、国际局势、非法移民和枪支管制问题,而不包括限制或拆分科技巨头。除非民意发生急剧变化,依靠选票上位的国会立法者当然不会认真推动一个不受选民重视的议程。
司法行动:仅有两起诉讼取得了一定进展
美国是适用普通法的国家,法院判决在其辖区内具备普遍的约束力(遵循先例原则),因此有“法官造法”之称。在反垄断方面,司法诉讼的影响力往往不逊于立法,而立法的实际效果还要依靠司法去实现。2019年以来,美国联邦监管者、各州以及普通当事人,对科技巨头发起了一系列的诉讼。目前看来,取得的进展并不大:
针对Alphabet的United States vs. Google尚处于举证阶段,开庭遥遥无期,看样子美国司法部难以提出过硬的证据;Epic Games v. Google已确定于2023年1月开庭,但是从Epic Games v. Apple的情况看,Epic获胜的希望不大。
针对Amazon的两起诉讼(Fremgen et al v. Amazon, D.C. v. Amazon),前者尚处于举证阶段,后者已经被无条件驳回。事实上,即使前一起诉讼继续发展下去,影响也很有限,因为它主要是关于电子书定价问题的,该业务占Amazon收入比例很低。
针对Meta的FTC v. Facebook,此前被部分驳回,此后FTC更新了起诉书。接下来,该诉讼将聚焦于多年前Facebook对Instagram和WhatsApp的收购是否损害了市场竞争,可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针对Apple的两起诉讼(Camera et al v. Apple, Epic Games v. Apple)取得了一定进展,前者已经庭外和解,而Epic v. Apple的原告诉求得到了法官的部分支持,导致iOS App Store的封闭性出现了一定松动。目前双方均已决定发起上诉。
上述案件名称足以令人眼花缭乱,我们可以根据原告的主要诉求,将其划分为四个类型:一揽子解决类;并购类;应用商店类;其他垂类市场类;重要性依次递减。
首先是一揽子解决类,意在指责科技巨头在某个巨大的、重要的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并试图对其施加全面限制(包括拆分、终止业务、巨额罚款等),一旦被法院接受,造成的影响将非常严重。例如,United States v. Google就是对Alphabet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及广告业务发动的一次总攻,D.C. v. Amazon也是对后者的电商平台业务发起的总攻。不过,司法诉讼就是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在大部分情况下仍有可能达成温和的庭外和解方案。
其次是并购类,旨在纠正科技巨头过去进行的损害市场竞争的并购行为,寻求业务拆分并制止今后类似行为的发生。FTC v. Facebook本来属于“一揽子解决型”诉讼,但在被法官部分驳回之后,转而聚焦于Facebook历史上的收购行为。如果本案取得令原告满意的结果,美国联邦执法部门可能发起更多类似的诉讼。
第三是应用商店类,主要是针对应用商店的封闭、收费过高、禁止第三方渠道行为,这些行为可能影响了应用开发者的利益。首当其冲的当然是Apple旗下的App Store,但Google Play也受到了波及。Cameron et al v. Apple, Epic Games v. Apple以及Epic Games v. Google均属于这一类型。在压力之下,Apple做出了主动让步,允许开发者通过电子邮件等手段接触用户、为用户提供绕过App Store付款的渠道。在Epic Games v. Apple的判决中,法官驳回了原告的绝大多数诉求,仅要求Apple允许开发者向用户提出其他付款选项,而Apple已经主动这样做了。
第四是其他垂类市场型,主要是针对一些规模不大、对科技巨头收入贡献不高的市场,例如Fremgen et al v. Amazon,指责后者在电子书领域滥用定价权。这样的诉讼影响有限,外界关注度较低。
上表列出的七个重要诉讼当中,两个已经终止;剩下五个在进行的诉讼都还停留在联邦地区法院这一级。美国的司法体系分为联邦法院、州法院两大部分;反垄断法是联邦法律,一般要在联邦提起诉讼,而联邦法院又分为地区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三个级别。目前唯一可能进入上诉法院的,就是Epic Games v. Apple, 双方都已经提出上诉。至于其他案件,要走完地区法院审理、判决、上诉、上诉法院受理的整个流程,恐怕可以拖到2030年。
美国的司法体系
资料来源:Judiciary Learning Center
针对科技巨头的诉讼进展不大,一方面是由于调查取证困难、法律概念适用不清;例如在部分驳回FTC v. Facebook的起诉书时,法官就指出FTC未能证明Facebook在个人社交网络市场有支配地位。另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反垄断执法部门的重视程度不足,例如United States v. Google就远远没有多年前的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那么快,至今也没有公开什么重量级证据。
归根结底,美国执法部门可能尚未在专业上做好进攻科技巨头的准备,现阶段发起的诉讼恐怕是表态的成分居多。从司法的角度看,许多联邦法官可能也并不认为科技巨头构成了对美国市场经济的严重威胁,不相信这样的诉讼有多高的社会意义。
美国联邦执法部门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举措,可谓“一蟹不如一蟹”:五十多年前对抗IBM时,美国司法部进行了长达十一年的顽强诉讼;二十多年前对抗Microsoft时,美国司法部进行了四年的诉讼,并迫使后者接受了伤害性不大、屈辱性较强的和解方案;如今对抗“四大科技巨头”时,美国司法部和FTC却连一个像样的起诉书都拿不出来。或许它们本来就不太想做这件事情?
“重要的是科技能够造福社会”
在2021年第四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Alphabet CEO Sundar Pichai被分析师问了一个敏感的问题:“我们看到美国国会提出了一大堆法案,看样子都是针对你们这些大型科技公司的。你认为这些法案有哪些可取之处,又有哪些不可取之处?”Sundar Pichai做出了直接而坦率的回答,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我们认为应当摘录如下:
“重要的是科技能够造福社会。因此,在很多地方我们都赞成监管举措。例如,我们曾呼吁推出隐私立法,尤其是在联邦层面保护儿童隐私。然而,目前国会提出的很多方案不是为了解决那些应该解决的问题。我们真诚地担心,某些立法方案会破坏我们向用户提供的一系列广受欢迎的服务,还会使我们一直以来在产品安全、隐私等方面投入的努力变得毫无意义。”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立法会将美国公司置于不利的境地,从而损害美国的竞争力。总体上看,当我们为一个产品添加很多功能时——要知道,我们每年在搜索业务上就会添加3000项功能;我们怎能保证每个功能都符合这些监管规定?我们是否需要主动提出申请,等待审批?监管有可能导向计划外的负面后果。我们非常担心这些规定对小企业和本地零售商的影响,以及对它们的客户的影响。”
“我说过,我们承诺要以建设性的方法做事。我们总是希望积极参与监管,从而让自己做的事情有利于社会。因此,我们已经敦促国会多花一些时间,考虑这些立法方案可能带来的计划外的负面后果。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聚焦于为我们的客户创造伟大的产品。”
稍早一些时候,Amazon开设了一个名为“支持小型卖家”的网站,反对国会正在计划的立法。在该网站上,有下面两段精彩的表述:
Amazon认为“八项法案”将破坏小卖家的利益
“国会最近提出了一批监管立法提案,目标指向包括Amazon在内的大型科技公司。如果这些法案得到实施,Amazon为第三方卖家开设市场的能力将受到严重损害,有可能导致数十万美国中小企业失去通过亚马逊平台获客的能力。这显然将损害小企业赚取收入的能力,并损害数亿消费者从我们的合作伙伴那里获得种类繁多、价格低廉的商品的能力。”
“我们承诺将持续为我们的第三方卖家的成功做出贡献。只要我们联合起来,就能向消费者提供任何人都不可能单独提供的良好体验。我们希望告诉你,这项立法意味着什么,也希望你的声音有机会被人听到。让我们一起努力让Amazon继续成为第三方卖家的乐园。”
我们本来还想补充一些东西,但是Alphabet和Amazon已经充分说出了此刻我们想说的一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互联网怪盗团 (ID:TMTphantom),作者:怪盗团团长裴培